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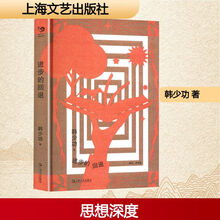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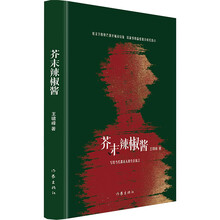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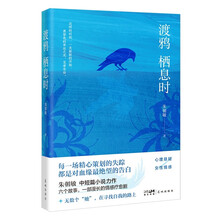
本书可谓中国版“忠犬八公”。在桂东南一座小乡村里,旺丁叔家的家犬阿黑以产优质的黑狗崽著称,不想某天竟反常产下一只花色狗崽,又遇上旺丁叔家大儿溺水夭亡,这只小花狗便被视为不详遭到丢弃;恰好“我”家闹黄鼠狼患,于是捡回了这只小狗,并取名阿花。少年和弃犬之间命运从此纠缠在一起,无论遭遇何种身不由己的逆境,两者都奋力一同向前奔跑,追逐属于自己的理想。
故事以“我”和小狗“阿花”之间的相互陪伴相互救赎为线索,将十数年来山乡人情风貌的变化一一呈现。既是对奋斗改变命运的人生隐喻,也包含了社会变迁发展的宏大叙事。文字真挚平实,兼具质朴和浪漫。
当天刚好是圩日,镇上丁字形的街道成了一个农副产品的大集市,人头涌动,寸步难行,更何况推着独轮车。聪明的旺丁叔带着兄弟们绕着圩边的道路走避开闹市,走上了弯弯曲曲的乡村公路。我坐在旺丁叔的独轮车上,其他兄弟推着家具,伴着车子轮轴吱呀吱呀的呻吟声前行。
过了圩镇,还得走三十里路才能到老家。路上有很多运送农资的各种车辆,汽车呼呼地加大油门颠簸前行,拖拉机则哒哒哒地爬行,汽车、拖拉机的拖卡哐当哐当地摇晃着行进,一路尘土飞扬。车上载的是化肥、氨水、石灰石之类的农资,还有一些农业机械,如插秧机、脱粒机、犁耙等。记得回家过年时,在村前鱼塘堤上看到远处村庄的墙上写着一行大字:“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可能这些农机下乡的动力就源于此。
这三十多里的回家路,还要经过一个叫“老圩”的地方。这个只有几间铺子的老圩坐落在一个小山坳上,像条脖子,名字的语音又和客家话的“老鼠”相近,所以乡亲们都叫它“老鼠颈”。大家在一间老圩卷粉店前停了下来,一人吃了一碟加了一块扣肉的卷粉,阿黑也吃了一碗粥,然后又继续上路。坐在独轮车上,我觉得这卷粉及扣肉,和老家驼背二哥做的一样好吃。
回到老家崖洞村,已经是傍晚时分。田间的冬种烤烟、小麦被裹上了一层暮色,村庄屋顶上的袅袅炊烟已经和暮色混在一起,分不清彼此。旺丁婶和乡亲们已在村口等候多时。
乡亲们有的拿着几只鸡,有的拿着两只鸭子,有的拿着一袋子米或米糠,有的拿着几把青菜,还有的拿着几斤红薯或芋头。我觉得这样的欢迎仪式有点奇怪:到了家再给我们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要老远地拿出来迎接呢?旺丁婶拉着我的手边走边说:“路上累了吧?到家了就好。”我想,很快就到山窝里那个热闹好玩的村子了。谁知道乡亲们把我们带到村口一个小平坡上的一座三间泥砖房前,叔伯们开始卸家具行李往屋里搬。这房子去年我们回老家和祖母过年时还没有。旺丁叔对父亲说,这块地是他寄回一百多斤全国粮票和一百二十元现金换的,房子是今冬兄弟们赶工建起来的,地面和墙面还不太干,但可以住了。听着这话,我闻到一股很浓郁的泥土味。在朦胧的夜色和昏暗的煤油灯光下,我看到这是一座一厅两房的屋子,一进门是厅,右边是卧室,左边是厨房、柴房兼鸡窝。客厅大门的右边墙角下,还有一个一尺见方的狗洞。乡亲们把东西放好后,和我们打着手电回村里旺丁叔家吃饭。村子广播声、孩子们的追逐声、鸡鸭找窝声、家人叫孩子吃饭声连成一片,在山窝里回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