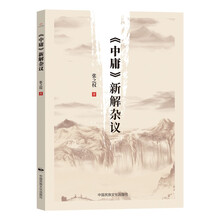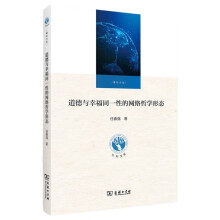看起来,这是一个由中世纪“圣战”思维模式所布下的世界迷局,尽管有学者试图寻找涵盖所有宗教教派的“全球伦理”,有“世宗和”等组织不断发起宗教教派的交流与对话活动,但收效甚微。只要“圣战”的思维模式仍在全球弥漫,只要宗教仍然是某些政治人物手中的廉价工具,这个世界谜局就破解不了。
中国,还有印度,可能是破解这个谜局的希望,因为他们拥有与“圣战”思维完全不同的文明传统,但前提是,他们是发掘各自传统以铸造现代主体性的成功国家。不成功,那就只是弱者对于世界和平的道德呼吁,没有说服力;只是获得经济成功,没有自身的文明主体性,那可能就只是“圣战”思维模式的模仿者,像日本走过的道路一样,也没有说服力。
坚持自己的道路并且正走向成功,是中国在当今世界所呈现出的状态,世界的经济格局因此而改变。但出于恰当解释“社会主义”的逻辑,我们太需要强调“中国特色”、强调国情特殊性了,所以走向成功的经验并未获得文明示范的普遍意义,在世界文明论坛上,我们只好讲讲过去的事情。我们甚至还需要采用带有阴谋论嫌疑的“韬光养晦”战术,拒绝讨论“中国模式”之类的议题,因为我们不愿意被当做“冷战”格局中一方阵营的新首领,而且事实上我们也确实讨厌那种角色。于是,“话语权”“失语”等,成为中国学者最纠结的话题。我们不仅没有话语去要求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我们甚至也没有话语来解释自己的国家成就。
原因只有一个,我们自己摘下了在世界范围内无不受人尊敬的礼乐社会、礼乐文明的桂冠,顶多也只愿意将它冠带在古人的头上。于是,在当今世界中国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主体性格,别人不清楚,我们自己也不清楚。
如果说我们尚不敢断言,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社会主义,本质上是对中国传统的礼乐社会的改造,是“旧邦新命”式的自我更新,那么至少我们可以说,社会主义与传统的礼乐社会有一点是相同的,即二者的秩序意识都着眼于社会全体,既不像政教合一国家那样将全部社会秩序都建立在单一教派的教义教规的基础上,也不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将社会主要秩序建立在单纯经济的自由运动上。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