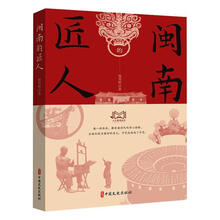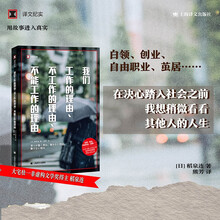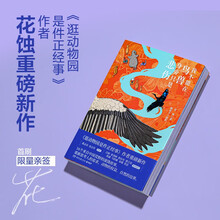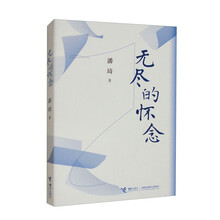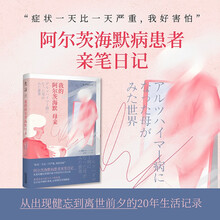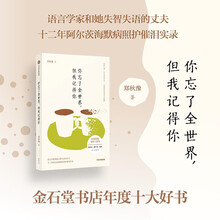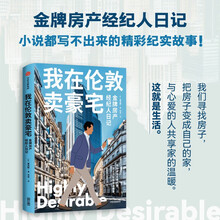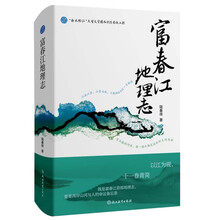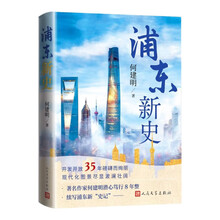《寻梦:追怀革命烈士傅文彩》:
渤海革命老区纪念园已建成好几年了,本想早去参观和瞻仰,阴差阳错竞几次都不能前往。今春陪北京来的客人前去凭吊,一进园区,被园内大气磅礴的建筑群所震撼,那白墙蓝瓦外观呈八边形围合状的纪念馆,那山丘之上雄伟壮丽的九层宝塔,那背面镌刻着渤海概况的栩栩如生的人民英雄群雕,还有那……,可未及细看,不远处的烈士英名长廊里传来哀伤的哭泣声。
近看,几名中年男女簇拥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婆婆顺长廊缓慢前行,在五万五千多名英烈中一行行地寻找辨认:寿光县,台头镇,傅家茅坨,傅文彩,主任,1918年2月生,1942年3月牺牲。“是他!”,突然老婆婆仆倒在地,放声大哭起来“爷(爸爸),可找到你了,奶奶、妈妈,我们全家人找你七十多年了!”。那穿透时空的哭诉,透着悲伤、委屈和无尽的思念。老人凄厉的哭声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人。
人们搀扶起跪在地上的老人。老婆婆迫不及待地询问工作人员,你们知道我父亲掩埋的地方吗?工作人员告诉她,傅文彩烈士与长廊巨石碑上所镌刻的绝大多数烈士一样,没有记载坟墓地址,也没有其他资料信息。听到回答后,老人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连声说“谢谢,谢谢!”老人红肿的眼睛里含满了深深的失望。
我的心猛然一颤,不自觉地朝老人走过去,想听老人说说心里话……第一章“父亲参加了革命”是约好时间到老人家里交谈的。那刻,院子大门和房门都敞开着,笔者不用敲门就直接进了她的家。
老人住在一座很整洁的小四合院里,院内大部分空闲地种植了时令蔬菜。连接大门口到北屋的是一条水泥方砖铺设的小路,进到室内,展现在眼前的是有些陈旧的家具用具,但整个房间收拾得有条不紊,叫人感觉舒适温馨。
老人早就沏好了茶,热情地让座、倒水。寒暄过后,老人谦笑道:“为了说得明白,我画了一张图”。边说边从衣袋里掏出一张老家院落自制图。
老人叫傅洪风,今年七十九岁,是傅文彩烈士的女儿,看上去身体还算硬朗,交谈起来吐字清晰、思路敏锐,语速虽不快,但历经沧桑的脸上却透着执着和刚强。
“这是四间北屋,三间西屋,东屋放置些杂物兼做牲口棚,南屋是觅汉(长工)住的,院子大门口朝西,门外是场院和枣树林,院子南面还有六分地的菜园。”老人一边指着草图一边述说着。那刻,老人仿佛回到了童年时代,眼睛也明亮起来,老人说:“这就我小时候的家,从我记事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都变化不大的家”。
院落图上标示得很清楚,字体工整,字义也准确。笔者询问过,得知老人并没上过学,只是早年间参加过村里办的识字班。老人接着说:“那时家里有良田二十四亩,还喂有大牲口,家庭殷实,在当地算个小康人家。”老人抬起头,用手捋了把额头上花白的刘海,一往情深地说起了家,说起了父亲。
我家是寿光县台头镇傅家茅坨村,祖祖辈辈靠种地维持生计。由于祖辈上勤俭持家,传续到爷爷辈上,日子过成了村里的上等家庭。我家从老爷爷开始三代单传,爷爷英年早逝,去世后才有了我的父亲,我们当地叫背生(遗腹子)。家里一直稀罕人,父亲就成了家里的宝贝疙瘩,真是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农忙时节,缠小脚的奶奶给地里干活的活计们送饭,颤颤悠悠,一头挑着水,一头挑着父亲,胳膊上还挎着干粮掾子。
奶奶二十一岁就守寡。在那个封建社会里,奶奶为了维护家族的声誉,一直没有改嫁。但是一个年轻妇女带着一个刚出生的孩子生活,那种不易可想而知!奶奶在外人面前从来都表现得很坚强,没流过眼泪。过日子有很多难事儿需要求助别人,但“寡妇门前是非多”,别人想帮也不方便接近。奶奶坚信有了儿子就有了盼头,这个家就有了希望,她暗暗发誓,一定把父亲抚养成有用的人,撑起这个家。
家里无论多难,奶奶也要供父亲读书。到了上学年龄,奶奶先是送父亲在本村念了四年私塾、读了四年小学堂,后来父亲又考人了丰城高小。
父亲没有辜负奶奶的一片苦心,无论在本村上学,还是去丰城,一直是班里的学〉-j“尖子”,他又乐于帮助别人,老师和同学都很喜欢他。到丰城念书后,父亲在学校住宿,十几天才回家一趟。每次回来,奶奶总是叮嘱父亲要好好念书,好好团结同学,然后烙上半口袋面火烧,有的火烧里还掺了红枣、芝麻。可是父亲总说不够吃,让奶奶多烙些。奶奶问过父亲,原来他在学校里用火烧换同学的面子(粗粮)吃,还经常接济那些生活有困难的同学。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