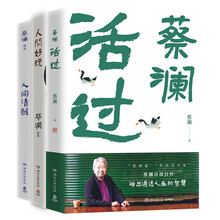从青年时代起,我便是在三点间运行。何谓“三点”?山、溪、桥是也。
山、溪、桥是太富诗意了,事实则不然。多少风雨、多少恩怨,都在山间、溪畔、桥头留下斑斑驳驳的旧痕。往事不堪回首,不堪回首却系心头。人生沉浮、一己荣辱,既已往矣,则似风、似云、似烟、似镜花、似水月;既似烟云,既似花月,也只是绰绰一梦,所残存的,不过是依稀的幻象——所清晰记得的,只是山、只是溪、只是桥。由此三者,我自编造了一个幻境——中国人只要提到它们,诗情便油然而生,不管既往是如何颠沛、坎坷,山、溪、桥编织的梦网,也便将人间的、人生的诸多哀痛、诸多欢乐过滤,只留下一腔超然如梦的意绪。此时,哀也无,乐也无,只有山间的溪桥,悄然如虹,只有桥下的流水淙淙而逝;一切都“无”了、“空”了——包括你自己。此刻,山耶?溪耶?桥耶?人耶?已然茫茫乎混沌一片。
这便是东方人的艺术灵感,东方人的超然情愫;凭此,东方人去化解悲愁、去配享大自然赐予的福慧。
刚满十八岁,我便到了贵阳,就读于师院中文系。学校在照壁山下;四年时光,也便抛于山下了。一九五八年,毕业后,分配到贵州大学,于是,便寄居溪畔;六年后,转调至省艺校,就此,在太慈桥边一羁十四年;一九七八年,又调回贵大,直至今日——又与溪为伴了。
这么一周转,从山到溪,从溪至桥,最后又别桥傍溪,四十年,在山、溪、桥间盘桓、周旋——人生的活动半径几许?不过二十公里而已。
孔夫子说过“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我呢,一纸录取书,便“落”山了,又一纸分配通知书,便“落”水了——至于到艺校,便连“纸”也不要——说一声,也便发“落”了。人生的道路,由自己选择的可能,是太稀微了。“落”到这里,“落”到那里,身不由己,这恰如飘蓬哩。但这途程,你要走下去——也只能走下去,不然,能奈何呢?既然是并不情愿地“落”到这里、“落”到那里,而又不能他走别涉,那么,就此“定”住吧,就此去寻求一种排解、一种慰藉。将人间世的哀愁,抛向山间、掷向桥下——任它随溪流飘浮而去。
四十年过去了,无可奈何人老矣。于无可奈何中,倒也炼就了自寻其乐的功夫,原是无可奈何地活着,而今,竟也“陶然忘机”了。日隐月居,溪流淙淙,灯火明灭,荒犬远吠——夜色如幻,我心空无。逝者如斯,“山”下的生活、“桥”畔的际遇,俱往矣;而今,依“花”傍“溪”,就此“定”住了。花开而复谢、谢而复开;溪水呢,流去的自去、流来的自来。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四十年都如此,而这四十年中,在“山”下、“桥”畔,有多少戏开幕、落幕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你得“闲看”,方能品味出这自然昭示的妙机哩。
“三一斋杂谈”的开篇,姑额之日“山水篇”。今日所谈,泛言而已。尔后,专谈花、溪、桥、山,乃至风月云烟。再后呢,是“嗜尚篇”,谈烟、酒、茶以及诸多怪癖奇嗜。接下去,拟谈“艺术”。每文千五百言,“杂”而已矣。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