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绝对不是一个英雄,我只是不计其数的善良的荷兰人中微不足道的一员。在那个黑暗恐怖的年代,他们所做的远胜于我。那个年代过去了,但对于我们这些见证者来说,关于那个年代的记忆,犹如昨日一般。那些曾经发生过的事,每天都在我们的脑海中萦绕。那样的日子永远不再来,永远。
——梅普·吉斯
第一次来到这个避难所,目之所及令我大吃一惊。整个房间一片混乱,到处都是大包小包的袋子、盒子和家具,一堆一堆的东西。我难以想象房间里的这些东西是如何搬进来的。或许他们是晚上搬的,又或者是星期天,公司关门的时候,总之我对此一点印象都没有。
在这里,有两间很小的房间。其中一间比较方正一些,带个小窗;另外一间房间虽然也有窗,但是比较狭长。房间是用木板隔开的,木头被漆成了深绿色,墙上的墙纸都有些泛黄剥落,而窗子上则凑合着挂着白色的厚窗帘。大房间里带厕所,边上还有个梳妆的地方。
再爬上几级陡峭的木楼梯,是一间相对大一些的房间,有水池、火炉和一些橱柜。这里的两扇窗子也都用窗帘遮了起来。离开这间房,再往上爬是个阁楼,有个小楼梯相通。那是个典型的阁楼,里面也堆满了各种包裹物件。
弗兰克太太和玛戈就像迷途的人那样,手足无措,无精打采。她们看上去好像动都不能动了。安妮和她爸爸则在尽力让这杂乱无章的房间显得井然有序,不断地搬移、归置、打扫着。我问弗兰克太太:“我可以做些什么?”
她只是摇了摇头,我建议道:“那我去拿些吃的上来?”
她默许了:“一点点就够了,梅普,拿些面包、牛油,或者牛奶也行。”
这种情形令人很伤感。我想还是让这一家人独自待着吧,不去打扰他们。我无法想象他们一家人现在的感受,抛下所有的一切:整个家、毕生的财产、安妮的小猫——莫特杰——还有他们所有的纪念品,以及朋友们。
他们就好像断然关上了自己的生活之门一样,一夜之间从阿姆斯特丹消失了。弗兰克太太的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
“莫特杰怎么样了?你见到我的猫咪莫特杰了吗?那个房客好好照顾它了吗,还是已经把它送人了?”当我们第二天一早去他们的避难所取今天早上的购物清单时,安妮问了一连串的问题,“还有我的那些衣服,那些小玩意,你从家里带了一些过来给我吗?梅普,你带了吗?”
弗兰克先生耐心地向她解释道:“梅普没有从我们家带什么东西出来,安妮……你难道不知道吗?”当弗兰克先生向安妮解释的时候,我听得出来,他暂时松了一口气。此前他一直都很紧张,而现在他表现得很镇定,可以看出他有了一种安全感。我知道,他这是在为其他人做沉着应对的示范呢。
安妮并没有问完她所有的问题:“我那些朋友们呢?他们都还好吗?都有谁还在那儿?还有其他人像我们这样躲藏起来了吗?有人在搜捕中被抓到了吗?”对于犹太人的搜捕,现在仍时有发生。
安妮有些激动,所有消息她都有兴趣。当她们一家人聚拢来的时候,我就和他们讲了昨晚和亨克一起去梅尔温德街的经过。他们对任何细节都不放过。
“住在你们家对街的约皮现在怎么样?她还好吗?”安妮在我讲完后问道。
约皮是安妮的朋友,和她年纪相仿,也住在亨泽街,和我们家对街相邻。安妮知道我有时会和约皮的母亲聊天。她是法国人,开了家女装店,她的先生是个犹太人。她先生是做古董生意的,他们家就住在那家牛奶店的楼上。有时候在我去买牛奶的路上会碰到牛奶店的老板娘,她总是一个人在看店。
“是的,安妮,我见到了约皮的妈妈。她还是老样子,他们家还是住在老地方。”
安妮的脸色沉了下来,因为她想知道更多关于她朋友的消息,她太想念朋友们了。
我向安妮表明,关于她的朋友们,我一点儿风声都不能透露。因为,这样做太危险了。
“外面的情况怎样?”弗兰克先生问,他坐不住了,急切地想知道外面的情况。
见到他们如此心焦,我将我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他们。我对他们说,针对犹太人的搜捕正在市内多个地方蔓延。我也告诉他们最新的反犹行动,是将所有犹太人的电话线路切断。他们留下的那张写着假地址的字条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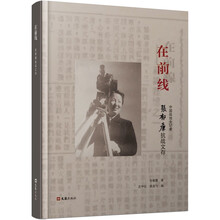






——《纽约时报书评》
★一个真正在乎他人的人书写的美丽文字,她的简单令人着迷。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