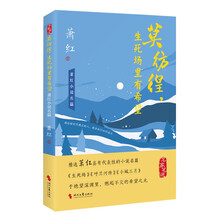《摇曳与芬芳》:
姚江发源于四明山的崇山峻岭,隶属余姚大岚镇夏家岭村东的米岗头东坡是它的源头,全长106千米,流域面积2440平方千米。作为一条河,百余千米的流程和两千多平方千米的流域,实在算不上大;但是,对于一脉对人类繁衍与发展有着卓越贡献的水系,姚城的母亲河,又无愧于这个“大”字。20世纪70年代发现的河姆渡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更是使这条全长仅百余千米的河流扬名世界,成为一条不折不扣的大河。
姚江之于人类的贡献还远不止这些。
在走出姚城之后,百里姚江沿四明山脚向东南方向逶迤蛇行,先后经鄞州、海曙和江北,于宁波市中心三江口与甬上另一条大河奉化江汇流成甬江,东流人海;在浙东沿海这片富庶的土地上,作了一趟精彩的惬意徜徉,把足迹嵌入大地;每一次逗留和洄折,都为世间埋下一个惊人的伏笔。古往今来,人们深谙大自然的这种暗示与提醒。于是,我们看到,百里姚江如一条精美的玉带,把余姚、宁波两座浙东名城与四明山串起来,其间尚有梁弄、陆埠、大隐、高桥等古邑名镇,更有河姆渡古文化遗址、梁祝故里、湾头、三江口等自然文化景观点缀,犹如一串华丽的项链,把四明大地装扮得熠熠生辉。而与京杭大运河的有机衔接,不仅让姚江自身成为大运河浙东段的重要组成部分,更使之有了一个面向东海的开放型出口,横亘中国南北的这条人工开凿的大动脉因此被激活,能量数以倍增。
所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尽管大河静时沉稳如岁月,深情款款,滋养着沿岸的土地和不息的生命;闹时亦可能暴躁如凶神恶煞,洪涝漫城,浊浪如潮,灾难与死亡席卷沿岸生灵。但是,又有谁能长久背离水与河流?当一个生命来到世间,其血管注定要以河流的形式流走于体内,躯体注定跟土地一样要接受血液的营养与滋润。水是组成身体最基本的物质之一。缺水的身体,其皮肤与毛孔迟早会板结、龟裂。而自然萌生的植株和草也都将枯死。
说来惭愧,作为一个宁波人,我对姚江的了解其实非常有限。居住在这个城市,天天为生计奔波,在江上穿梭往来,行色匆匆,极少静下心来好好看看身边这条江,乃至淡忘了水位、水色和退潮时沿岸泥涂面积的变化。这条河距我们如此之近,又如此之远。
它的存在似乎跟我们的生活已不再有关联。它跟我们世代相伴,予我饮予我渔予我灌溉,我却无动于衷。
我想起某位前辈说过的一句话,他说衡量人的身体健康状况,就看器官给人的暗示,如果所有器官都正常,让人忘却了它们的存在,那就是健康;相反,若老有某些个器官提醒或暗示着什么,让你时时惦记着它,那就有问题了。这或许可解释为我为何会淡忘身边这条江的原因:它已经成为我们生活、身体的一部分,它一切正常、安好,以至于被我们忽略。
但是,果真如此吗? 三十年前,我曾与姚江有过一次亲密接触。那时我尚年少,暑期随大人坐船去湾头割猪草。湾头是姚江流至市区时一个回头望月围挽出的一片土地,人称“小三江口”,地处近郊。也许受姚江水滋养的缘故,湾头的蔬菜长得特别好,是甬城的一大品牌,有“宁波的菜园子”之誉。姚江的水养菜,也养草。那时农村家家户户都养猪,猪多为患,以至于乡问田头能作为猪食的草越来越少。于是人们想到去湾头割猪草。种菜下脚料多,老菜帮烂菜叶可以用来做猪食,当地人就懒得理那些疯长的猪草,吸引西乡许多农户农闲时大老远摇橹背纤地赶过去。
那是一次奇妙的经历。木桩船以一支橹为动力,在窄窄的塘河上晃悠了半天,忽然豁然开朗,进入一条大河。这是作为少年的我有生以来见过最大的河,开阔程度超过了想象。那天多云偶有雨,远远望去,河面上水气缭绕,雾茫茫一片;水无声涌动,不见它流,船在上面却能感到一种雄浑的力量。水色凝重,介于青与浑之间,让人觉得那样的水更厚重、更有内容。船在这样的水面漂逐,如一片叶子轻泛。两岸散乱地排列着一些树、一些芦蒿和一些瞅不清面目的庄稼。我眼尖.不远的水岸边漂着一群细细的麻点,时聚时散,聚时水面成了张大麻饼,散时像一张大大的蛛网,一只只“蜘蛛”随波盈动……是野鸭。船靠近时,一部分野鸭被惊起,扑喇喇从水面掠过,洒下一溜水线;胆大的向外侧散散,自顾怡然嬉耍、争逐。
船缓缓前行,还没从怡人的野鸭嬉水图中回过神来,船头、两侧突然溅起一片白花花的银箔,仿佛水下有什么机器在发射。那些银箔大的几尺,小的有巴掌宽,在空中穿梭、乱舞,让人眼花,然后一头SLA水里,消失不见。其中有两片一头栽人船舱里,跳跃,翻腾,噼啪作响。我扑过去,把大的那片结结实实压在身下。那是一尾肥硕的胖头鱼,足有五六斤重。
船到湾头已近傍晚,暮色下的小三江口,在一个少年眼里已经不能用河或江的概念来界定,而是一个湖泊;雾白洋洋,当时脑海里闪过这个词。晚餐是在河坎上挖的一个地灶上做的,用钢筋锅子炖了一大锅白煮塘鱼,那个鲜。
这样的姚江,注定会给少年的我留下一片活色生香、抹也抹不掉的记忆。
三十年过去,无须我刻意验证什么,大家都清楚,那样生猛的姚江早已消失不见,只能留待追忆了。
几天前,我途经解放桥,无意中瞄了眼窗外的姚江,看到的是一摊浑浊的灰水和大片让人心惊的泥涂…… 河流流向它想去的地方,在有的地方强调了自己,在有的地方隐忍了自己。河流有它自己的行走方式。一条河流的长度,是它自己丈量出来的。河流向前,也给两岸以滋养,浇灌出有水色的文化、习俗。当一条河流死了、涸了,最大的不幸不是两岸的生命,而是河流自己;而把河流引向穷途的,往往是我们人类。大河流水,它能丈量出自己的长度、时问的宽度,却丈量不出人世和人心。
幸好,大河不死,姚江仍在,一切还来得及。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