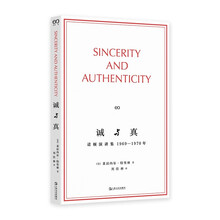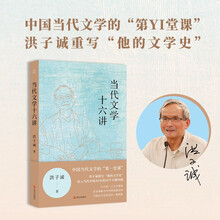二、另一种现象的分析:托多罗夫
茨维坦·托多罗夫在将本身创造出一种新美学的“巨著”①和大众文学加以对比时指出:“还是有那么一个幸福的领域不存在作品与文类之间的辩证矛盾,即大众文学的领域。习见的文学名著只属于自己的文体而不能归类于任何其他文学文类;而大众文学名著确切讲就是那么一本与其文类极为契合的书。”(《散文的诗学》,第56页)人们会惊讶于后一种定义:如果也存在“大众文学名著”的话,怎么可能不涉及那些或多或少与其所属文类决裂的作品呢?否则,从什么方面去识别它们呢?这种论断在我们看来是草率的,至少理由不够充分。引入注目的著作,不管副文学还是非副文学的,都命运多舛,并不总能立即被认可。在这方面,夏洛克.福尔摩斯最初经历的例证是非常有意义的:故事的新颖并没有一下子引起公众的追捧,断裂效应、读者的痴迷在一段时间之后才跟上。
托多罗夫在另一部著作中发展了他的思想。对于他,只存在副文学“文类”,因为被他称为“文学本身”的文本是通过其独创性、相异性(仅仅是相对的,他明确指出)③和新颖性来定义的:“不能满足这一条件的文本就自动转入另一个范畴:那边是所谓‘大众’文学、‘通俗’文学的范畴;这边是经院写作的范畴。”(《散文的诗学》)如果托多罗夫认为一切非名著的东西都应搁在“通俗”文学拥挤而低价的书架上,正如目前的情况那样,那么他的观点我们无法苟同。为什么要把侦探、历险、科幻、魔幻或情感小说家与模仿创新者的人混为一谈呢?一部“糟糕的”小说也是文学作品。“流行”作家并不都是平庸的作家、模仿者、自随者……
他们可能也以重复的方式坚持使用一些秘方,他们反复地讲,并不让苛刻的读者感觉意外。无论如何,我们得承认托多罗夫看到了两种对立审美倾向的(和平?)共存:一种在于抬高唯一性,追求令人手足无措的稀有的审美感受;另一种则相反,充满重复性,受着经过长期实践证明的方法导引。那么,马丁.伊登所说的被普遍纳入“劣文学”的“副文学”因此是以内在重复机制的重要性为特征的吗?事实上,事情并非那么简单。首先,除了“副文学”,还有许多其他文类,甚至连给一种“文类”下定义都是一件冒险的事。我们只需回顾一下让一玛丽.舍费尔所说的:“类属的逻辑绝不是单数的,而是复数的:根据一种属性例证,一种规则应用,一种家谱关系或类比关系存在的标准,‘把文本进行分类’能讲出一些不同的东西。”(《什么是文学文类》,第181页)。因此,一种文类将同时是:全部文本属性及物质、结构、实用限制(期待视野,阅读契约);一系列规则及形式与审美惯例;一种作品传统及互文空间,具有复制、偏差、对立和超越的机制;所有超乎历史联系、具有相似性,尤其是主题相似的著作。①我们能证实:首先,所有文学文类从本体论上讲都在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着不同程度的重复;其次,副文学的重复有其自身的特殊性。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