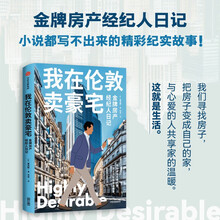病危中的路遥路遥病倒在延安并被确诊为肝硬化腹水后,曹谷溪马上给我打电话,说:“路遥得的不是好病,还不知是什么结果呀!”我一听,大惊,当天就赶往延安。一路上我的心情十分紧张,不知到延安后会看到什么样的场景,脑海里总闪现体验过的生死离别。到病房一看,反倒松了一口气:他比健康时瘦了几十斤,看上去倒恢复到了年轻时的模样了。他一见我,立即坐起来拉住我的手,眼泪就要往出溢,我坚定地摇了摇头,对他说:“不要紧。我们弟兄天生就是来克服困难的,没有困难,我们会感到空虚。”他静静地看着我,努力地笑着,没有让眼泪流出来。看着他竭力忍耐悲伤,我反而忍不住了,鼻子发酸,喉头发僵,口干得要命,只想于呕。他也看出我的忍耐,又恢复了“大哥式”的平静,说:“咱们到院子里走走,这里不时就会来人,说不成话。”我们来到院子里一个小草坪上,那里有一套石桌凳,但我们没有坐,而是盘腿坐在草坪上开始“拉话”。
他简要地介绍了自己的病情后,笑着问我:“现在是生死关头,你凭感觉说,我能过了这一关吗?”我说:“能。”他说:“为什么?”我说:“咱们弟兄都是在干石板上扎根,钢丝绳上走过,什么困难没经过?我想要死,也在猝然之间,老天不会给你提前打招呼。”他说:“你这道理太勉强了,哄三岁娃娃也不行,还拿来哄我。”我说:“真的不是哄你,我觉得你现在模样和年轻时一个样样的,充满了朝气和自信,完全不像个病人。”他笑了笑,再没问我,两人又说起了小时候的事,说到高兴处,竞大笑起来。就在这时,护士要他回房间输液,他这才收了笑容,对我说:“我现在是又病又累啊。看望的人太多,简直支应不过来了。”我说:“你支应什么呢?你是病人,他们是健康人,你怎么舒服怎么来啊。”他说:“不行啊。上次有个同学来,我当时实在无力坐起来,躺着打了个招呼。那人就不高兴了,找到咱们的老师,说我架子大,不理人。为此,老师还跑来说了我几句。”显出十分委屈的样子。
回到房间后,果然有好几个人等在那里,有的提着点心,有的拎着水果,有一位还拿出笔记本要路遥给他写几句话,说:“这是个难得的机会。”我连劝带哄把他们请了出去。之后,我对曹谷溪说:“能不能限制一下看望路遥的人啊。”并转述了路遥的难处。曹谷溪说:“路遥现在病得‘反反沓沓’了。看望的人多了,嫌烦;来的人少了,又觉得‘空’得慌。”一听这话,我的心一沉,突然觉得路遥可能真的不行了,忍不住流下泪来。
路遥转院到西安后,我去了好几次,只见他的病情一次比一次重。有一次,我一进去,他就拉着我的手,很沉重地说:“海波,我肯定是不行了,肯定要死了。”我说:“你胡说些什么,不是好好的吗?”他说:“我不胡说。
省长也来看过我了,你想,如果不是不行了,省长能来看我吗?”一句话就把我噎住了,好半天想不出来个说辞。
又有一次,我去看他。他的神色特别好,很兴奋地对我说:“我现在想出一个办法来了——让老家人把当年产的各种粮食捎来和起来熬着吃,说不定会起作用。”我嘴里虽然附和着,心里却无限悲凉,感觉到他在作无谓的挣扎。
还有一次我去看他时,他的五弟正在旁边,好像是在洗碗什么的。趁五弟走开时,他突然问我说:“我好像记得我五弟和你大儿子同岁,是不是?”我说:“好像差不了多少。你怎么问这个?”他好一阵没说话,显出深思的神情,最后才叹息着说:“现在想起来,老家人做的事也不一定全无道理。如果像你一样也早早结婚,说不定儿子也这么大了。”过了一会又说,“我现在最想念的是老人,父亲、母亲、奶奶和大爹、大妈。这些人虽然没文化,但在人生的总体把握上比我们强啊。”这时候我明白他“不济事了”,多少年筑起来的精神堤坝完全崩溃了。我仍试图劝慰他,他制止了我,说:“说什么也不顶用了,能做的事只是人生的总结。海波啊,你知道我现在最难受的是什么吗?是很想见女儿一面,又不能见。我知道这种打击迟早会落在女儿头上,我能做到的只是尽量地推迟到来的时间啊。”说到这里,他哭了,我也哭了;他用纸巾揩去了眼泪,我没有,只是用力晃动着脑袋,把眼泪甩向两边。
这是我最后一次和他说话,我再一次来时他已经昏迷了,不省人事了。那次和我一块去的还有两个人,他们是城市里长大的,还特意买了一大束鲜花。我们在远离病房走廊入口就被挡住了,护士不让我们进。全凭路遥的四弟王天乐从里边出来,把我领进去,那两人却没能进去。我也没能进入房间,只在走廊里隔着窗子朝里边望了一眼,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有生命的路遥。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