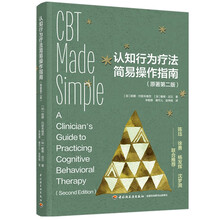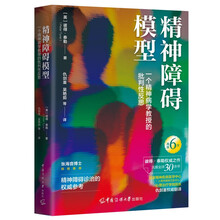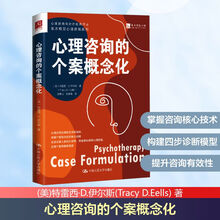不足为奇的是,这个版本的一系列争议和独断的立场没有减少,更因为应用了投票诊断增加了它前者留下的可质疑的方面。例如这个版本首先是通过取消了同性恋作为一个诊断,取而代之是自我矛盾型同性恋去取得认同,然后无声无息地在没有解释的情况下妥协(说明,自我矛盾型同性恋)就不算在精神问题里面了。同性恋是否是一个诊断(这些作者相信它不是),问题在于令人惊讶的投票诊断而不是用研究实证的精神病理学。这个过程由DSM委员会加强了,往往私底下缺乏正确性地对加减诊断作投票。
现在的DSM导致了现在的抑郁症时代,就如1960年代的米尔顿,以利眠宁和安定为标志的焦虑年代。现在是因为过度诊断抑郁症并配给处方抗抑郁药物,我们预测抗抑郁药物也会走上同样的轨道。这个倾向表现为对处理日常生活的问题都用抗抑郁药物应对,威克费尔德和霍维兹谴责它去掉了伤感作为生活中正常和信息化的情感。这些同样的作者总结出的越来越多的文章反映了相关的抗抑郁药物的无效性,特别是在轻微的病例中,还会伴随着惊人的一系列的副作用,很多都是非常严重的。精神病学家卡雷特果断地总结为心理治疗可能更加有效,也不会如抗抑郁药物一样对身体健康有破坏。
他的看法受到越来越多行业内外专家的拥护。
一些症状和征兆组合在一起被起名为了各种综合征而找不到原因,然后没有心理治疗干预了,病人都吃药了。每一个症状,表面上都能处方一种药物。尽管我们现存有许多的精神抑制药,却只有太少数的分类。
而往往同样的药物会处方给不同的症状。比如,抗抑郁药不仅处方给抑郁症,也同时能处方给强迫症、戒烟、对工作不满、性欲低下、早泄、饮食失调症或者其他多种可质疑的文献建议的问题。
更深一层,焦虑和抑郁也如头痛或者发烧那样的诊断,它们后面可能隐藏着很多的疾病。因为DSM—IV包含了重新改组的同样症状来冠以新的名称,这就导致了如曼内德的批评,责问我们可能不是在对付一种疾病(心理疾病),而可能是对付一系列不同阶段的症状。
在没有确定性,只强调可靠性,用达到意见一致的方法来决定诊断的方法是没有发展前景的。每个人都看着一系列的症状总结为同样的“诊断”,甚至即使这个,人同跟真正的疾病没有关系。这就远离了科学确定性。它的缺陷是偏向社会和政冶观点达到一致意见而不是根据需要治疗的疾病本身。更确切的是,达到一致是靠临床经验(但大部分人的经验都只是看个感冒发烧,不代表他们是专家)。
到了2010年,非精神科的医生—一那些看诊身体的疾病已细致到从病因为导向的医生们,他们完全接受了DSM-IV的术语,也变成了主要的精神抑制药处方的源头。他们是85%的精神抑制药物的处方者。这在中国是不同的,就在本书编写期间,新生模型被引进到了中国。数十年来,中国的医生和普通群众都接受了中文里面等同躯体化的词语,如“神经衰弱”。DSM-III的出现和医药公司代表进驻中国市场的后果是,精神病学抛弃了心理学概念,就像美国一样,开始接受症状/抑郁的概念,同样的确定性和药物滥用的问题也都出现了。对比美国,中国无论是医生还是普通大众都更能接受神经衰弱和躯体化的概念。
这解释了为什么滥开处方药的行为只在中国精神科医生中存在,而没有娑非精神科医生效仿。
伴随着放弃精神神经症,我们很快轻视了兼顾病人的历史和应用心理测试。现在主要使用的简短的抑郁书面筛查测试都很不准确,特别是早已过多的爱操控人的AXisII病人们看上去会因抑郁来寻求住院躲避麻烦,然后在适当的时候或麻烦过去的时候看上去恢复正常,他们就能按自己意愿离开医院。
让我们看看有哪些因为现存的社会和政治偏见而存在的更可耻的非科学决定。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