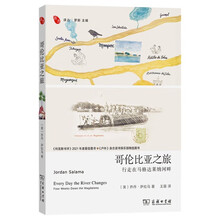剪纸婆姨
老郭元的母亲去世了,她是村里辈分最大的女人。
她在半年前就病了,刚开始时,还能在窑洞前的太阳地里坐坐,后来就不见了踪影。询问病情,家里人说是胃里难活,吃不下东西。农村里无医无药,就那么抗着,直到把人给抗没了。
她去世的那天夜里,我们几个知青还在熟睡,身边的同伴突然把我捅醒,他说,幼民,你听!我于是听到了我一生中感觉最恐怖的声音。
像一阵阴风呼啸着掠过山顶,在村庄上空盘绕;像群狼一样的哀鸣,尖利得撕裂了夜空,那是从人的喉咙里发出的不似人声的嚎叫,随着风,清楚地送进了每一个窑洞的窗户,听得我心惊胆战,不禁用被子蒙上了头。
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当地的风俗,在人咽气的那一刻,家里人要走出窑门,沿着山路,走到村里最高的地方,呼喊他的名字,将他的灵魂送往遥远的西天。
老太太儿孙满堂,直系的旁系的加起来近百十口子人,一同放声,在寂静的夜晚,蓦地响起这凄厉的哭喊,直叫人毛骨悚然,仿佛冥间和尘世在此刻重合了,茫茫的夜色变成了地狱之门。
第二天一早起来,这村庄好像变了个模样,没有了人们上工的吆喝,没有了牲口出圈的嘈杂,甚至连鸡狗都不曾发出声响,冷清得就像被冻结了一样。
老太太的儿子们头系孝带,在村口向每一个过往的人跪拜磕头,这也是葬俗中的一项,孝子们代表亡者,这一拜,便了结了世间所有的恩怨,让远行者无所挂牵。虽然我们也知道这个规矩,但看到白发苍苍的老汉在我们晚辈面前下跪,还是被弄得手足无措。
知青是外来人,可我同样感到了悲伤,这不仅缘于和老乡的情分,还因为老太太对我有很大的恩惠。
陕北的女人在村里多半没有名字,郭元的爹叫长茂,老太太嫁到村里来时,就被叫做长茂婆姨,后来变成了郭元妈,再后来就被叫成了奶。我从她孙女那儿打听到,其实,老太太曾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杏儿。
杏儿不是本地人,很久以前,她是随着家人逃荒到这个地方的。陕北这个地方,称北边叫上头,往南,叫下头。杏儿的老家,听说是在上头的黄河边,具体地点,已经无人知道,反正很远就是了。杏儿的家人把她留在了这里,又继续南下了,杏儿就成了一个没有娘家的女人。
那是一个蓝花花的年代,女人们的命运大多很悲苦。杏儿独自在陌生的土地上生活,一定有许多不为人知的难处。但杏儿还是幸运的,她并没有因为失去娘家人的庇护而受到欺负,这一是因为长茂为人忠厚老实,二是因为杏儿能干。
我们村位于延河北岸,闹红的时候,是根据地的边儿,对面当时是白区,这儿就成了来回拉锯的地方。长茂在区上工作,敌人一过来就撤到北边去了,家里的事儿就全都丢给了杏儿。杏儿上有公婆,下有几个小叔子,再加上自己生的孩子,一大家子人的吃喝穿用,全靠她一个人来张罗。
杏儿麻利,再多的活儿也难不倒她,洗衣做饭,推碾子磨面,带孩子伺候老人,里里外外一把手。我听秀儿说,她奶背着小娃,领着大娃,照样吆喝牲口拉磨,一会儿簸,一会儿扫,抽空还能给娃娃喂口奶,干完了收拾回窑,磨盘上干净得连个谷碴都剩不下。
那时陕北人穿衣,全得靠婆姨们纺线织布,杏儿一家人口多,棉花少,远远不够用,杏儿就想出了换工的办法。她向宽裕的人家借来棉花,织成布,自家留一半,还给人家一半。杏儿织布又快又好,平整紧实,所以,许多人家都乐意与她换工,每年棉花收获的时节,杏儿都要忙碌一阵。虽然是土布衣衫,可经杏儿手一缝连,全家人在村里,也是体体面面,整整齐齐。村里其他家的婆婆如果嫌儿媳妇手笨,总会说,你看看人家杏儿的针脚!知道老戏的人都夸长茂是董永,把个七仙女弄回家来做婆姨。
杏儿一共生了五个儿子,长大后个个是劳动好手,人也都忠厚老实,在村里颇有威望。他们家虽不算富裕,但有了杏儿的勤俭持家,倒也吃穿不缺,平安度日。到了土改的时候,就给定了个中农。不像村里的另一家,贩牲口把家底都输光了,倒落了个贫农。长茂和杏儿并不在乎这些,靠自己双手挣饭吃,心安理得,管它成分是什么。
我插队到村里的时候,老太太已经不太干活了,只是看着媳妇们忙里忙外,顶多说上两句,就不再言语。她虽然年近七旬,可腰板还是直直的,面庞清瘦,皱纹细细的,爬满了全脸。但从眉眼的结构可以隐约看出,她年轻时,应该是个俊俏的婆姨。
有一天,我到郭元家去吃饭,家常饭也没有什么好说的,我却一眼就看上了他窑洞窗子上贴的窗花。春节时贴的窗纸,过了大半年的时间,早让烟熏得黑乎乎的,满是窟窿,窗花也被风雨褪掉了颜色,淡淡的只显出些影子。但这模模糊糊的窗花,却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我问郭元,这窗花是谁剪的,郭元说,是俄妈冒铰下的,你还能看下?
陕北虽然剪纸出名,但并不是人人都会剪,我们村那么多户,就没有一家贴窗花的。所以在郭元家里看到,多少让我感到意外。陕北民歌里唱道:“生女子要巧的,石榴牡丹冒铰的。”会剪窗花的女子,个个是人尖尖,看来郭元妈也不是个等闲人物。我喝着小米粥,心里却在盘算着把这些窗花弄到手,谁叫咱自小学画,就喜欢这些东西呢。
第二天,我就跑到公社的供销社,买了几十张麻纸,拿到郭元家,要给他们换窗纸。老郭元一定认为我脑子有毛病了,不年不节的,竟然自己掏钱给他家糊窗户。陕北人一年才换一次窗户纸,这下提前过年了,只是不知为什么,当看到我把烂窗纸卷起来拿走时才恍然大悟。老郭元骂我道,你这娃,想要窗花揭走就是了,还破费买什么纸!老太太很高兴,可能从来也没有人这么看重她的剪纸。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