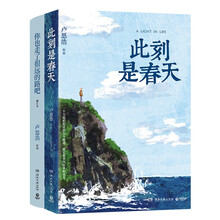2016年12月4日晚北京
站台
那个身怀春光的少女Ⅰ
台风快要来的时候,我一个人在马路上,没有撑伞。为了告别我的大学时代,2011年一个潮热的下午,我随意在论坛里进了一个北疆约伴的帖子。帖子很吸引人,于是打包好行李,一个人从香港飞往乌市。
发帖人就是妖。那晚,我们约在五一夜市吃夜宵。沿街羊肉串的叫卖声此起彼伏,大桶大桶的啤酒,毛豆配花生。夜市里人头攒动,每一个犄角旮旯都塞满不大不小的桌子,五六个人叉着腿尽情吃喝。妖是最后一个到的。那晚,我们如网友见面,例行自我介绍。她小脸儿煞红,梳了一头非洲脏辫,一口闽南口音。
还好都是旅行中人,不扭捏造作,立马就熟络起来。一路上,她总是靠在半开的车窗上,脏辫甩在日光充足的公路上。在天山南北的光景里,我们说说笑笑,消耗着生命。
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的。
车开到琼库什台,那是一条只能徒步穿越到喀拉峻的古道。下车后,我们收拾好行李,随手找了根木棍,就进山了。走着走着开始下雨,后面还下起了冰雹。妖说,走南闯北这么多年也没见过六月下冰雹的。我们只好避雨。夜色渐黑,体力透支,加之没水没食物,已经赶不到预定的上车点,手机也没了信号。
妖冲我喊:“你这个混蛋,下雨天非要走这条野路子!”
当时,我也很慌,从没见过这种环境和场面,不知如何是好。
“总要找个地方先睡一晚吧,在外面会被冻死的。”说完,妖就拿着手电筒,把冲锋衣武装到鼻子,只露出眼睛,甩着一头脏辫,右手拿着木棍,消失在黑夜里。那一刻,她像身怀武功的女侠。
妖再跑回来,已是半小时后了。她找当地村民借了一个牛棚暂时落脚,弄了几床被子、一桶水。我们吃了最后一碗泡面,汤渣都喝得精光。雨还在下,牛棚漏雨,门也关不紧,雨滴淅淅沥沥落在被子上。两个无助的小混蛋在苍茫山野的一个小牛棚里分享食物、水、温暖和秘密。
第二天一早,眼睛被木门缺口射进来的光线刺醒。妖打开门,打了一个激灵——下了一整晚的大雪,草原已经被埋在下面。雪还在下,妖裹着被子站在门口,白雪把她的脸映得很白。我坐起来帮忙生火,火起来的时候牛棚里烟雾缭绕。那一刻,我坐在一团烟雾里,内心油然而生一种英雄主义,像一个劫后余生、满血复活的小战士,庆幸自己还能看见第二天的太阳。
再后来,警车开上山巅……我们被50公里外赶来的110救走。
在青春里,我们总会有这样误打误撞的旅行、任性不设防的相遇,来去自由,果敢倔强。我们在路上分享阳光和秘密,惺惺相惜,微风拂过,带来的都是美好的音乐。在这条公路上,你与遇见的人,或挥手告别,或继续同路,他们是时光里的旅人,身体里分泌着引人入胜的春光。
身怀春光的少女Ⅱ
2011年的最后一天,妖对我说:“我想去冰天雪地看一场壮美的日出!”
于是,我买了2张去坝上的火车票,坐了8个小时,又转乘7个小时的汽车,裹上这辈子穿过的最厚的衣服,套上最多层的袜子,戴着最傻愣的帽子和耳罩,赶在2012年第一个日出前到达了那里。
回北京后,我带妖逛胡同,北二环护国寺旁有一个百花深处胡同。狭窄的胡同儿口,墙壁上长满了绿色的苔藓。胡同儿里很多人家在二楼养了鸽子,所以经常看到它们掠过头顶,却很少有人问津。她说想要一个百花深处胡同儿的铁皮门牌号,一直想要。于是,我们挨家挨户敲门,有的炒着菜当作没听见,有的理都不理直接把我俩看成怪物。
妖说:“我们偷一个吧?”
我哪儿偷过东西啊,但不知怎么回事在妖的推推搡搡下居然同意了。
第一次作案是当天晚上。我们在胡同儿口吃好晚饭,等待夜幕降临。妖在胡同儿口把风,我作案。那是第一次做贼,没有经验,心里跟吃了炸药似的,怦怦乱跳,只要听到风吹草动、猫叫狗叫,就立马收手。其实,我俩紧张得很,大概在胡同儿里盘旋了10分钟,偷门牌的事就无疾而终了。
妖回厦门后,一直惦记着她的铁皮门牌。那一年她生日,说无论如何也必须给她弄一个。那天,我下班后,专门找后勤阿姨借了一个扳手,坐着地铁,路上一直在想这次应该怎么偷,万一被抓了应该说什么。到了百花深处已经是晚上了,几个大爷在胡同儿里遛弯儿,窗内时不时飘出做饭的气味,头顶的鸽子有节奏地拍打翅膀。每次,当你觉得四下无人准备举起工具动手时,总会从黑暗尽头驶过一辆自行车,或从墙上窜出一只猫,吓得你魂飞魄散。
我在胡同儿里来回踱步,拿起电话拉大嗓门假装与人通话,或是停在路边像是离家出走的少年,踩一踩脚下的易拉罐儿,弄出一点儿动静,或者扮成一个迷路的游客走走停停,好像被此处吸引又不得不离开的样子。整场表演,没有一个观众,黑暗的胡同儿里,我像一个带了妆的孤独小丑,演了好几出没有人看的肥皂剧。
终于,四下都安静了,炒菜的关了窗户,大爷们回家泡脚,阿猫阿狗也都累得趴在一边。我拿起螺丝刀,蹭到一户人家门口,刺啦一下就把门牌抠了下来,脱下衣服包裹起来,撒腿就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的家,一路惊魂未定,时不时看看衣服里的门牌,还在,就好。
再后来,我们一起旅行,去了很多地方,拍了很多照片,写了一些矫情造作的文字,骄傲地宣告我们都过得很好。回望那个在乌市初次见面的夜晚,根本就不会想到两人一起冒险,做了这么多混蛋的事情。每当想起5年前无意中点开那个帖子,那一坨励志要环游世界的傻子,居然在后来的某个夜晚,成为一个赴汤蹈火、有情有义的小偷。嗯,掐死她的心都有了。
庙街里失传的美味
药劲上来的时候,我穿过狭窄的楼道,按下电梯,汇入庙街的灯红酒绿中。四面传来人们的交谈声、商铺里的砍价声、酒杯碰撞声、歌厅的歌舞声,乱七八糟地在耳边嗡嗡作响。因为感冒的缘故,脑袋一阵绞痛,霓虹变成虚影,在眼前晃来晃去。此时,只有一碗滚烫的粥能解救我。
这就是住在庙街的好处,24小时都能吃到想吃的食物。找一处摊位坐下,一碗窝蛋生滚牛肉粥上桌,稠稠的白米在碗里冒着气泡,趁热咕噜咕噜喝下去,出一身大汗,感冒已好了一大半。我在庙街住了一年有余。刚来香港的时候,觉得这里很酷,一副港片里打打杀杀的模样,每个细节都充满故事性,仿佛一阵迷迭香飘来,肉身便被这味道深深蛊惑。于是,很快找了房子,交了租金,买床、买柜、买厨具,从内地抱来被子和棉絮,就在庙街安了家。参差不齐的灯箱和广告牌是香港的专属美学。沿街凉茶铺就有好几家,我爱喝夏菇草,清热解肝火。便宜好吃的烧腊店是我每周末的加餐食堂。到了夜晚,街道上支起摊位,霓虹从地上一直亮到几十米的高台,这里的黑夜没有尽头,灯火不灭。各色小吃摊位好像从地下莫名其妙地钻了出来,白天的花店变成小吃摊,五金杂货铺变成小吃摊,连无人问津的一根电线杆旁也支起了小吃摊,大家张灯结彩,拒不收摊。直到每个人的细胞都被美食填满,云层才舍得遮住月亮,渐渐收拢。
那时还是穷学生,庙街刚好是平民消费,每晚熬夜苦读后就会去楼下吃宵夜。我住的四喜楼出门直走,过两个路口左转,有一家非常小的泰餐店。没有门面,整间屋也就10平方米,所有的家当都摆在面儿上。老板是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头儿,笑起来脸上的皱纹在炎炎夏日能挤死好几只苍蝇。老板娘是泰国华侨,每月往返泰国和香港两地,把当地的食材带回来。那天晚上,有些凉意,雨丝儿胡乱飘着,依然有些学生仔和老街坊在路上晃悠。我饥肠辘辘地坐下来,老头儿给我做了饭,然后撑起一把大伞。老板娘又回泰国去了,他一个人照看着店面,索性坐下来和我聊天。他是一个乐天派,聊到高兴的事情会开怀大笑。在香港,会笑的人都很珍贵。当朋友间相互打趣时,他的笑声响亮、坦诚、真实。他的脸上仿佛写着“好心肠”三个字,因为他经常会免掉我的一些零碎钱,也会在炒饭时多给我加几片肉,或用温柔的语气说一声“再见”,从不冷脸对人,更不会像有些店家那样把盘子冷冰冰地放到桌上,脸都不转过来。
他炒菜也很好吃,热心肠的人做出来的东西多半也不会差。店里的主厨、店长、服务员都是他,有时老板娘会来搭把手,但做菜的一直是他。我喜欢他做的香叶肉碎炒饭、冬阴功汤,还有咖喱牛肉,量足管饱。他的水平不像大厨,却贵在家常。他的厨房就是一个露天灶台,看起来并不干净,却每每做出光洁如新的厨房也诞生不了的美食。这是一个神奇的露台,只见他挽起袖子,几滴油入锅,手里的大勺在铁锅里来回翻动,不用怀疑,肯定有了。
在漫长的庙街岁月中,我成了他的常客,有时一坐下来,不必点他都知道我要什么。说来,自从17岁离家至今,一路北上南渡,吃过的各地风味数不胜数,大多也就停留在“好吃”的程度。但这个老头儿做的菜,却能让人吃出纯棉的质感,冷的时候吃了暖和,热的时候吃了清凉。一边吃一边还有人笑眯眯看着你,让你慢点儿吃,说着“锅里还有”。
毕业后我就离开香港,成为一名“北漂”。5年后,我回了一趟庙街,穿过几条街,就找到了那家店。老头儿在里面摆弄着什么,门口摆满了各种香料,露台和铁锅都不见了。他抬了抬头,看到我,笑眯眯地说:“我记得你啊,是那个大学生啊,好久没看到你了。”
“你的店怎么变样了?还做泰国菜吗?”我说。“早不做了,没人过来吃,年纪也大了,就关掉了。现在卖一些泰国的特产,我老婆从泰国进的。”他答道,面孔一点儿没变,热情,爽朗。那时,我还是个学生,没吃过什么山珍海味,觉得他家的味道就是最正宗的。如今他年纪大了,不做菜了,想是连铁锅都拿不动了,这一脉,算是失传了。
那些名字故事的开头发生在我的大学教室。在南方那个潮湿的天气里,除了铁,什么东西都会发霉。教学楼的小格子里,每天重复的事情单调而沉闷,似乎永远不会发生改变。
晚上,自习室往往只有两三个人,都低着头认真温习英文。我是到教室蹭网的。白炽灯吱吱地响,几只不怕死的蛾子扑在上面。外面黑得出奇,一过傍晚就暴雨倾盆,下个没完,总让人觉得要发生什么大事。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