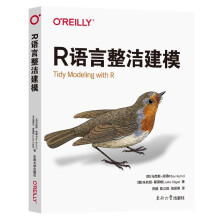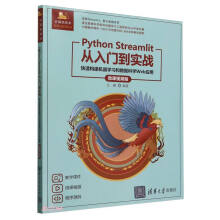从以上所述可以见出,官方对电影事业的重视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了,区区一部电影动辄惊动官方高层,甚至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当然不能排除一些领导从个人角度对电影艺术性的认可甚至置重,但是,这种高度重视主要是从政治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的,看重的是电影对公众广泛而深入的影响,从而将电影视为进行主导意识形态宣传和教育的政治工具,而对于电影的艺术性即便不是忽略也是轻描淡写。
而大批电影艺人(包括电影导演、编剧、演员、摄影、美工等各种具体的电影生产人员)、一些电影评论家及个别电影艺人出身的管理者,基于时代的政治本位的文化语境,在重视电影政治意义或意识形态功能的同时总是努力地寻求电影作为艺术的审美因素,尽可能地为电影增加非政治的成分,包括审美的、生活的、娱乐的、甚至商业的因素(当然这些因素往往是难以分离地融合在一起);但是他们在这种文化权力场中的位置和力量决定了特定时代中他们的未必悲壮的失败。
“新时期”之前的中国内地电影事业的运作基本上是以政治为本位的,无论是管理模式还是制作理念.都是将电影视作政教工具,“文革”期间这一情况可谓登峰造极。过分的政治情结和意识形态偏向,经常导致影片的公式化、概念化现象,结果是演绎了政治,疏离了生活,缺乏趣味性和观赏性,从而也冷落了观众。官方高层似乎意识到了文艺中这种过分政治化所导致的僵局,在提出了“双百”(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引起了文化尤其是文学艺术短暂的活跃和繁荣,但紧跟而来的“反右”运动,以所谓“毒草”和“香花”的敌我战争思维模式对许多曾为文艺建设真诚提出建设性意见的文艺界人士进行了严厉的政治批判和打击,结果在实质上等于否定了“双百”方针,使之徒具标语口号的仪式性功能。
电影也在频繁而又一波三折的文艺和政治纠缠一起的运动中踉跄而行,而这种枯燥单调的文艺政治运动无非是文化权力场域中权力资本的不断运作而已。布尔迪厄说:“场是力量关系的场所(不仅仅是那些决定意义的力量),而且也是针对改变这些力量而展开的斗争的场所,因而也是无止境变化的场所。”①依此而观,“十七年”电影事业实际上也是一种场,也是不同力量斗争的场所。至于场内不同力量的斗争,布尔迪厄这样进一步表述:“在一个场中行动者同体制不断斗争,他们是根据构成这个游戏空间的规律性和规则(以及在特定的紧要关头超越那些规则本身),使用不同程度的力量,并因此有了不同的成功的可能性,来占用在游戏中处于危险境地的特殊产品。”②就是说,不同力量、场内的游戏(斗争)规则、相互关系以及斗争目标这些要素都是一定场内的斗争的必要构成因素。作为文化权力场的“十七年”电影事业,既然是不同力量斗争的场所,也当相应地存在着上述组构因素。层次繁多的电影管理机构和连篇累牍的电影政策(文艺政策对作为艺术分支的电影自然也普遍适用)其实就是“体制”因素;那些努力争取电影艺术自主权和自由度(当然是部分性的)的电影艺人(包括一些电影评论家和极个别本属于体制力量的管理者)就是“行动者”;而这里所谓的游戏规则往往是由体制力量制定和掌控,而且常常被体制力量所凌越;斗争的目标无非是对电影事业权力资源的争夺。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