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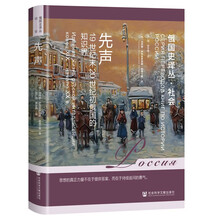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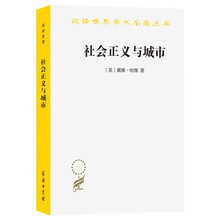


本书讲述了十位“草根英雄”的人生故事,她们不幸遭遇职场性别歧视,饱受性别刻板印象之苦,于是诉诸《民权法案》,以此作为法律依据提起诉讼。她们的案件最终都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在漫长的审理过程中,她们又经历了诸如失业、离异、重病等人生不幸。然而她们从未放弃,在亲友、律师、法律团体、学者、记者等的帮助下,她们的胜诉最终改写了美国历史,切实改善了美国女性的生存环境。本书作者吉莉恩·托马斯是美国公民自由联盟高级专职律师,她基于自己多年的从业观察,选取这十个标志性的案件,深度采访案件当事人、参与案件的律师和专家证人、案件涉及机构的工作人员等。本书曾入选《大西洋月刊》“理解美国政治的33部佳作”、《纽约时报》女性历史月10本推荐图书。
1964年,美国众议院就《民权法案》议案进行辩论的最后一天,一位议员提出,在法案第七章“就业机会平等”的条款中,应该在“种族”“肤色”“宗教”和“民族”之外增加“性别”。当《民权法案》正式颁布时,“性别”一词得以保留,该法案因此成为美国性别平权运动的里程碑,成为美国职场女性的福音。
育有幼儿的母亲遭遇招聘歧视,产假归来的新手妈妈被迫离职,男上司对女下属频频性骚扰,职场“女强人”因“不够有女人味”而升职无望……本书中的十位主人公遭遇不同形式的职场性别歧视,她们以法律为武器,勇敢地提起诉讼,最终诉至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她们的故事鼓舞人心,她们的胜诉界定了《民权法案》第七章的范围和影响,让所有女性得以寻求曾经仅对男性开放的工作职位,争取平等薪酬,不再因结婚和抚养儿女而失业,不必忍受性骚扰和恶意的工作环境。
本书作者吉莉恩·托马斯是美国公民自由联盟高级专职律师。通过细致调查和深入访谈,作者描绘了近五十年来美国反职场性别歧视的历史变迁。在维护平等、公正的漫漫长路上,那些敢于跨出第一步的女英雄们,值得被铭记。
第4章 恶意工作环境(节选)
美驰联邦储蓄银行诉文森案
繁华的乔治城十字路口处,一家五金店楼上的小律所内,朱迪丝?路德维克的新客户哭个不停。那是1978年9月,路德维克第二次会见米歇尔?文森。她是一位娇小的非裔美国女性,20岁出头,想要离婚。就像拉帕波特律师事务所在报纸广告上承诺的一样,她们的第一次会面是一次15分钟的免费咨询。(律所名字显示有“多名”律师,未免有虚张声势之嫌。路德维克是所内唯一一个律师,擅长处理小额离婚和遗嘱案件。)现在文森重新回来并签署了委托代理合同,向路德维克支付了275美元的固定费用。路德维克在文森的收据上盖上律所印章时,不知为何,文森开始流泪。她告诉路德维克,她对自己的工作感到很痛苦,并且“再也难以忍受下去”。路德维克很是疑惑:“你要忍受什么?”
路德维克回忆说:“她开始向我讲述。那太可怕了。我目瞪口呆。”
文森后来证实,三年多来,她在首都联邦储蓄银行(以下简称“首都银行”)的管理者悉尼?泰勒一直对她进行性虐待,不是强迫她性交或口交,就是摸文森的胸部和臀部,或是尾随她进厕所,暴露自己直挺的阴茎。他粗俗地形容口交为“舔鸡巴”,会把文森逼到角落里警告她,“今晚你要和我做爱”。
1974年秋,19岁的文森入职后不久,这一切便开始了。文森在哥伦比亚特区东北部长大,首都银行的罗德岛大道支行就在她家附近。她在这家支行拥有储蓄账户。银行规模很小,文森与两个出纳员和经理泰勒都相处得很好。自15岁从高中辍学之后,她从事过一些工资很低的兼职工作,但一直希望能在专业的环境中工作。一天,她在停车场走向泰勒,询问银行是否有招聘计划。第二天,泰勒给了她一份实习出纳员的工作。接下来的四年,文森表现出色,获得了高度评价,时常取得绩效奖励,最终晋升为副经理。
文森刚开始在支行工作的时候,泰勒待她“如父”。泰勒已婚,是七个孩子的父亲,还是所属教会的执事,他似乎很符合自己的角色定位。他从银行门卫一职开始打拼,成为当地黑人社区的成功典范。泰勒在文森面前就像一个导师,鼓励她就专业和私人问题向他吐露心声。他借给文森银行业方面的书籍,即使她并未加班也向她支付加班费,并称之为努力工作的奖金。当文森告诉泰勒她正与丈夫分居,新公寓的保证金还差120美元时,泰勒给了她这笔钱。“他假装自己很体贴,”数年后,文森告诉记者,“仿佛非常乐于帮助你。”
文森确实需要这份帮助。在成长过程中,她和当环卫工的父亲一直关系紧张,并曾多次离家出走,以至于她的母亲曾试图将她送进领养中心。为了逃离糟糕的家庭,15岁的时候,她接受了家族的一个年长朋友的求婚,先是怀孕,以便使未达婚龄的她可以合法成婚。但在和新婚丈夫的一次争吵中,她流产了。
在首都银行工作近六个月后,文森和泰勒去一家中式餐厅共进晚餐。他们在一些其他场合也曾共进晚餐。据文森所言,正是在那儿,泰勒首次向她提出了非分的要求。文森拒绝了,但向泰勒保证她会感激泰勒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我不要你感激,”他告诉她,“我想和你上床……我能给你工作,也能炒你鱿鱼,我能成就你,也能毁掉你,如果你不按我说的去做,我会杀了你。”
餐馆旁边就是一家汽车旅馆,泰勒开了一间房。“我不知如何是好,”文森后来告诉记者,“这是个让我信任的男人……他一直在跟我说我现在是个大女孩了,说他不会伤害我,并脱下我的衣服。我就站在那儿,什么也没做。我像块木板那样僵在那儿,就好像一具死尸。眼泪顺着我的脸流下来。他什么也没有说。他只是在做他想做的事。他脱下我的衣服,让我躺在床上。事情就是这样。”
文森曾希望泰勒一旦得手就会放过她。但虐待逐步升级。(不出所料,记录显示文森那年请了23天病假。)文森后来证实,自第一次之后,他们曾发生40到50多次性关系,通常是在银行里——在地下室甚至银行金库的地板上。文森觉得自己无力逃脱。她需要这份工作。这是她维持生活的唯一来源。此外,她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自汽车旅馆的第一晚后,泰勒就一直威胁说,如果她不好好配合,就杀了她。当文森抵抗他的侵犯时,泰勒使用更暴力的手段来强奸她。在经历了不止一次这样的虐待后,文森因阴道撕裂而求医。
文森后来解释说:“我眼前一片漆黑。我找不到一条出路。我没有参加互助小组,也没有任何可以商量我所经历的这些事的人。这就是我一直忍受这么久的原因。因为害怕。”不出所料,在被生活中出现的这个男人虐待了数年之后,文森开始怀疑是否还有其他的生活方式。“你开始接受在你身上发生的这些事,”她反思,“即使你打心底知道这是不正确的。”文森的身体明确地告诉她,自己正承受着极端的压力。她开始掉发,不能进食,并患有慢性失眠。
……
路德维克从未听过“性骚扰”(sexual harassment)一词,但她确信文森描述的这种性虐待行为违反了《民权法案》第七章。回想起自己的理想主义,她哑然失笑。“我从未想过,”她说,“法律对此不予保护。”
自女性走出家门开始工作,今天我们所称的性骚扰行为便存在了。但20世纪70年代末时,这一术语才刚进入大众话语体系和法律视野。正如弗雷德·施特雷贝在其翔实的法史著作——《平等:女性重塑美国法律》里所描述的那样,“性骚扰”一词由康奈尔大学人类事务项目的三位教授于1975年初首创。该项目提供了一系列社会正义课程,其中包括一节由琳·法莉教授的有关女性和工作的课程。某个大学物理实验室的秘书卡尔米塔·伍德曾找到法莉寻求帮助。在忍受了其上司——该实验室的负责人——三年来的窥视、抚摸和其他性侵犯行为之后,伍德辞职了。伍德的辞职请求曾被拒绝,因为负责听证会的工作人员认为她离职仅仅是“出于个人原因,而非具有说服力的理由”。
法莉和她的同事苏珊?美耶及卡伦·索维涅都希望帮助伍德。她们知道伍德的煎熬并非个例,她们从自己的女学生口中听过这些骇人听闻的故事,在此前的工作中也曾亲身经历,但她们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来应对。法莉、美耶和索维涅向全国约百名律师发出呼吁,为伍德提供立案的指引性意见,并请求开展运动来声援和伍德有相同经历的女性,但她们苦恼于如何简洁地表述伍德的遭遇。在经过深思熟虑并否决了一些词语(包括“性强迫”“性恐吓”“性敲诈”)后,她们找到了一个合适的词语—“性骚扰”。
法莉、美耶和索维涅代表伍德所做的努力获得了理想的效果。时任纽约市人权委员会会长的埃莉诺·霍姆斯·诺顿在1975年4月就女性在工作场所的权利举行了听证会,法莉在会上直接讨论性骚扰问题。“大多数男性管理者将这视为一个玩笑,最多认为这‘并不是什么严重的大事’,”法莉在作证时说,“更可怕的是,公然反对骚扰者的女性有可能突然被视为一个疯狂、古怪甚至放荡的女人。”一个月后,康奈尔大学人类事务项目在纽约州伊萨卡市就性骚扰组织了一场“畅谈会”。近20位女性向一小群人详细讲述了自己的经历。畅谈会被合并至一个新的组织——职业女性联合会(后更名为职业女性协会,并迁至纽约市)。
这两起事件引起了《纽约时报》记者伊妮德· 内米的注意。于是,1975年8月,她发表了《女性开始公开反对工作中的性骚扰》一文。这是“性骚扰”一词首次出现在全国性出版物中。(并不是所有的女性都欢迎这个带有贬义的新标签:一位女编辑在《哈泼斯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语带讥讽的反驳文章。她写道,骚扰,“或者,有些人称之为调情,”“给女性早上精心涂抹口红提供了一个理由,还有可能是下午4 : 30女洗手间中的一个话题。”)不久后,《华尔街日报》发表了其与此问题相关的第一篇文章,20同月,《红书》杂志开展了一项调查,请读者记录下自己所遭遇的性骚扰。1976年11月,一篇分析该调查结果的文章称这是一场遍布于“行政套房、速记室和……流水线”的“瘟疫”:在超过9 000份的调查结果中,有90%以上的人称曾遭遇一种或多种形式的性骚扰。“无论男性还是女性,来工作时都背负着一生的情感包袱——他们幼时被教导什么是男子汉气概,什么是女性特质。文化迷思和社会本能决定了男性和女性对待异性的方式,”该文总结道,“我们才开始解开这一包袱,开始仔细审查它,努力置换其中的老旧过时之处。”
女性通过诉讼来“解开包袱”的努力带来了复杂的结果。种族骚扰早在1971年就已被视为非法的种族歧视的变体,性骚扰却很难取得进展。法官们不愿把“性别歧视”的标签贴在他们看来只是不太理智的挑逗行为之上。因此,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许多法官对指控上司虐待的起诉状都不加理会,他们认为:“你不能因为一个男人尝试挑逗就指责他。”
这些早期的案例十分俗套:男性管理者向女性下属提出非分之求,女性下属拒绝,男性管理者解雇女性下属。一位名为保莉特?巴恩斯的女士是哥伦比亚特区环境保护署的一名秘书,在拒绝上司的求爱后失去了工作。法官驳回了巴恩斯基于第七章提起的诉讼,称这只是“对不和谐的人际关系过于敏感而导致的冲突”。在亚利桑那州,眼部护理巨头博士伦公司的文职工作人员简·科恩和热纳瓦?德韦恩选择了离职,不愿继续忍受管理者无休止的语言和肢体骚扰。法官驳回了她们的反歧视诉讼,认为管理者的不当行为“似乎只不过是一种个人的癖好、倾向或是习性”。
一位加利福尼亚法官驳回了玛格丽特·米勒基于第七章提起的诉讼。玛格丽特因为拒绝“迎合”上司的性要求而被辞退。法官判决,这样的要求不可能是“基于性别”的歧视,因为它们太过于普遍,难以规制。“女性对于男性的吸引力以及男性对于女性的吸引力是一种自然的性别现象,这种吸引力在大多数的个人抉择中至少都发挥了微妙的作用。”在新泽西,阿德里安娜?汤姆金斯也因拒绝管理者的非分要求而被辞退。法官对她基于第七章提起的诉讼置之不理,因为该法并非旨在“对发生在公司走廊而不是小巷之中的、被性欲激发的人身侵犯提供联邦层面的(人身伤害)救济”。
正如这些判决所显示的,男性视女性为性对象(当她们表示不情愿时就将之抛弃),这被认为不受第七章的保护。其他形式的歧视是对某一特定群体明确憎恶,与之相反,性骚扰则被许多人视为由吸引力所致—这是一种赞赏,而非侮辱。此外,将管理者的性侵犯行为视为一种纯粹的“个人”行为,与其被赋予的工作职责无涉,这也意味着该管理者的雇主不会因此承担责任。
正如女权主义法学家凯瑟琳· 麦金农在其1979年的里程碑式著作《对职业女性的性骚扰》中所详细描述的那样,最初,涉及特定骚扰者和骚扰目标的性骚扰法律还是一片真空。与种族骚扰不同,法律未能将性骚扰视为更宽泛87的社会结构下发生的事件。在这一结构下,男性群体仍旧操纵着世界,女性群体仍旧是次等公民。正如麦金农所解释的那样:
男女关系的确被认为是私人关系,但这一事实无法掩盖它巩固了女性在工作场所和整个社会中居于附属地位的事实……一旦这种“私人性”被置于等级化的社会结构内,那么,对每个人来说,这种关系将无异于种族关系。
麦金农解释称,要改变法律对性骚扰的处理方式,需要说服法院接受两大意义深远的原则:其一,骚扰行为并不仅仅是某个男性受到某个女性的吸引,这是“基于性别”而产生的,因为受害者的女性身份是其受到骚扰的缘由;其二,工作环境中不受欢迎的性行为并不仅具私人性质,它直接且负面地影响女性受雇的“条款、条件或特别待遇”,这是大多数男性从未体会过的。
1976年,联邦法院首次承认性骚扰属于性别歧视,认定性骚扰“为女性的就业制造了人为的障碍,而另一性别却不受影响”,趋势开始扭转。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其他一些法院也作出了有利于原告的类似判决。更为鼓舞人心的是,保莉特·巴恩斯、简·科恩、热纳瓦· 德韦恩、玛格丽特·米勒以及阿德里安娜·汤姆金斯最终在各自的上诉中都得到了推翻原判决的结果。
这些成功案例的共同点在于,提起诉讼的女性均拒绝了上司的性要求。毫无疑问,这种示好是不受欢迎的,并且这些女性均得以证明自己“品性”良好。此外,她们都曾因自己道德正直而受到处罚:都曾被解雇或被迫离职,并因此遭受有形的经济损失。凯瑟琳·麦金农将此种骚扰命名为“交换条件”(quid pro quo,拉丁语意为“以此换彼”),将被求欢描述为拟定交易中的一部分:屈服于我,你继续保留工作。
但麦金农还界定了第二种骚扰,它曾经,并且至今仍旧更为普遍:“工作环境”骚扰,即现在广为人知的“恶意工作环境”。她如此描述符合此类行为的典型特征:
女性遭遇令人讨厌的求欢,可能仅仅因为她有着女性的躯体,这种遭遇可能成为她日常职业生活的一部分。在工作中,她可能经常被抚摸或揉捏,被色眯眯的眼神打量,视奸,被突袭偷吻,被肆意评论,被刻意孤立,在工作上被欺负,但这些从不会明确地和她的工作相关……作为一种工作环境,性骚扰通常不需要女性明确回答同意与否,便可作出进一步行动。丢失工作的威胁在交换条件型性骚扰中显得更为直白,在此类性骚扰中则较为含蓄,但其胁迫性却不弱于前者……这涉及“虚与委蛇”,绷紧神经,保持警惕,有技巧地示好并能暗示双方关系中的性尺度或性可能,同时避免直接向她询问“这样如何”,以免招致她的公开拒绝。
米歇尔?文森的遭遇并不完全符合其中任何一种形式的骚扰。尽管文森称悉尼?泰勒曾将自己的性要求和解雇她的威胁相联系,这是交换条件型性骚扰的典型特征。但与那些成功的交换条件型性骚扰诉讼的被告不同,作为管理者,泰勒从未继续实施这些威胁。他无须如此,因为文森妥协了。并且,与那些胜诉的当事人不同,文森从未蒙受任何可量化的经济损失。反之,她获得了最高的评价、绩效奖励和职位晋升(在最终的诉讼中,银行承认这些都是文森应得的)。
文森所描述的泰勒的胁迫性性行为——抚摸、窥视、暴露自己——在很多方面符合“工作环境”性骚扰的特点。在工作日期间,泰勒会前往街上的脱衣舞酒吧,回来后,他会在文森以及其他女性银行职员面前仔细阅读色情杂志。在文森没有被强奸、抚摸或窥视期间,她的工作环境也被“性欲化”了。
从未有法院梳理过这些一团乱麻似的事实。事实上,在朱迪丝·路德维克困惑于该如何处理米歇尔?文森案时,凯瑟琳?麦金农的书尚未出版。
导论
第1章 有孺之妇
菲利普斯诉马丁·玛丽埃塔公司案
第2章 突破“细细的蓝线”
多萨德诉罗林森案
第3章 长命百岁
洛杉矶水电局诉曼哈特案
第4章 恶意工作环境
美驰联邦储蓄银行诉文森案
第5章 “保底,不封顶”
加利福尼亚联邦储蓄信贷银行诉格拉案
第6章 成为“女合伙人”
普华诉霍普金斯案
第7章 可能会怀孕
国际工会、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诉江森自控有限公司案
第8章 “我会一直告到桑德拉·戴·奥康纳那儿去”
哈里斯诉叉车公司案
第9章 不要向报信者开枪!
北伯林顿与圣达菲铁路公司诉怀特案
第10章 “每个女人都应拥有安全分娩的机会”
扬诉美国联合包裹服务公司案
尾声
致谢
注释
索引
这是十位坚强女性的故事,她们努力工作,诚实生活,却遭遇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和阻力,这一切只因为她们是女性。人人生而平等,都有自我选择的权利,性别不是决定命运的关键,一个健康的社会理应赋予每个人展现自我的机会。
——何勤华,华东政法大学原校长
透过改变女性职场环境的十个典型案件,可以发现女权主义的演变过程以及不同形态。当然,诉讼策略只能以法律上的形式平等为基础,往往很难涉及结构内部的权力关系和实质性问题。为此,我们需要多维的观察视角,需要在正义、照料以及互惠之间达成适当均衡。生物学上的性别固然不可改变,但社会、文化上的性别概念是可变的,因而也就可以成为社会进步的一种驱动装置,既可重构政治格局,也可影响知识理论。
——季卫东,上海交通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今天,女性在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的地位大幅提升,“女性以牺牲、服务为荣”的说法越来越站不住脚了。崛起的女性力量既挑战了传统社会观念,也动摇了原本的社会结构。但这个改变过程中一定会出现倒退,正如这本书中勇敢的主人公们也曾遭遇困境,如果没有她们近乎倾尽所有的抗争,平等和公正只是遥遥无期的愿景。
——黄佟佟,专栏作家、娱评人
法律有其种种限制,比如政治,比如地域,比如时间。但从观念的意义上,身为女性,我们都将永远受益于这十个案件,而观念会比一切东西都走得更远。
——李静睿,作家
在本书的十个案件中,我们反复看到个体的愤怒、痛苦、不公感与群体无意识的对抗。强大的法治社会无须害怕这些愤怒的声音,相反,受伤者的恐惧所暴露的往往是社会自身的软弱和偏见。吉莉恩?托马斯没有为读者构织一个凯歌前进的性别平权神话,而是通过不同案件的反复、曲折,向我们展示了“平等”本身的复杂性。
——焦姣,上海大学历史学系讲师
在美国法制史上,法律与社会运动之间的联结从未像近半个世纪以来这样紧密。女权形成运动,运动催生案件,案件塑造法律,法律改变职场。作者通过对十宗大案的描摹,将这一链条丰满有力地呈现出来。她的笔调朴实无华又热情昂扬,帮助读者体味当局中人的抉择、徘徊与坚持,让法律的变革走向生动,走近生活。
——阎天,北京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
她们为之抗争的事业最终获得了支持,她们所提起的诉讼成为经典案件,她们仍默默无闻,本书所讲述的正是她们的故事。
——琳达?格林豪斯,普利策奖得主
这是“她们”的故事,记述了女性为女性所做的牺牲,也是“我们”的故事,与每个人息息相关。我们承诺保护女性的尊严和平等权,是她们成就了美国。
——劳里?利文森,洛约拉马利蒙特大学法学院教授
吉莉恩?托马斯以精准而优美的文字讲述了界定《民权法案》第七章范围和影响的十个案件,这些原告和律师是真正的英雄。
——《波士顿环球报》
吉莉恩?托马斯做了细致入微的调查,写出这样一本让人受益匪浅的书,她拥有讲故事的天赋。
——《纽约时报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