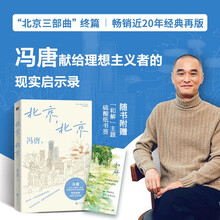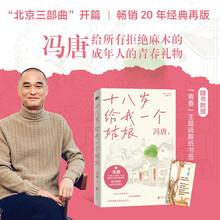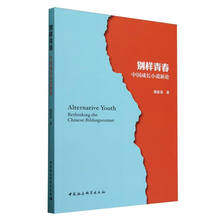《华侨文化研究书系·海外星空:华文创作三地域》:
尽管也有来自泉州永春侨乡的台湾诗人自白,余光中一样的“本我”失落,如名诗《西螺大桥》所言:“既渡的我将异于”“未渡的我”,“彼岸的我不能复原为”“此岸的我”。尽管也有加拿大华侨诗人洛夫一样的“悲剧”感喟:“诗永远是人的颂歌,也永远是人的哀歌。诗的思辨色彩,也主要在现代人的人生悲剧的感喟。”但诗人黄河浪却能写出“来港”的否定和故土的肯定,写出两者之间的“复杂的情绪”——以“新生”,写“新见”;从“这边”,看“那边”:感悟到回归前的香港,并非都是“风景这边独好”。如,诗人曾表现其“水泥森林”中的“沉重”生活,在《节奏》歌吟:“喘不过一口气/来去匆匆/再把剩余的血/喂第二份工/生活的节奏/打在胸口上/像打桩机一样沉重……”东方明珠,国际城市,现代光辉,却到处都有历史的阴影:“波音七四七”与“人力车夫”杂陈,虽是“在现代铁鸟的翼下”,“全世界近在咫尺”,却甩不掉“拖人力车的老人”,那一双“瘦骨嶙峋的手”,“还拉着上一个世纪”的重负在拖(《东方风味》)。而失踪的少女:“像一条迷途的孤舟”,“随波而来”;色情交易“展览在簾幕之内”,“赤裸疔疮”,“溃烂在文明的脊背”(《香江潮汐》)。这种现代光辉与历史阴影的对照,所造成的人欲横流,人性反常,人格变形,人心扭曲,人情淡漠,在香港回归前王一桃的《香港诗辑》,也能听到对比的声音,痛苦的歌吟。但王一桃重在“香港”与“臭港”,即“透视鱼目和珍珠”、“看穿丑恶和美善”的对比对照,黄河浪却旨在“这边”与“那边”的对照对比。在认识“这边风景”阴暗面的同时,诗人也在思恋“那边风景”的靓丽、诱人,写了大量歌颂祖国锦绣河山和故土生活风貌的优质诗篇。其实,黄河浪诗歌创作的这种对比对照原则,遵循的正是雨果的艺术原则,但又都已“移植”于《故乡的榕树》的散文创作之中了。或者可以说,正是散文创作的这种艺术原则,启发了诗人诗歌创作的艺术构思的——因为诗人创作的散文与诗歌的两头,本就有这么一条直达的艺术通道。
故乡的榕树,就在这一艺术通道孕育,就在散文的那一头诞生,就在诗人的艺术大观园成长。有成就的作家,是很讲究艺术多样性多手笔的,是致力于构筑自己的艺术大观园的。从泉州侨乡走出来的印尼泗水归侨、著名老诗人蔡其矫,曾翻译秘鲁诗人聂鲁达的诗作,很赞赏聂鲁达的艺术观,认为诗人的艺术表现,不能只有一种现实主义,不能只有一种艺术手法,要有艺术的多样化——即聂鲁达名言所示:“一个诗人,如果他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就会毁灭;可是如果他仅仅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同样会毁灭。”认为“聂鲁达继承了惠特曼的传统,但又加进了风行二十世纪的超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法。传统与革新,从来都是相携并行。”要继承传统,要革新,要创新,有志于文学事业者,概莫能外。《故乡的榕树》艺术大观园的营构,即以此为审美依据。其文学视野,有民族文化和传统美德的交相辉映,有历史感和现实感的经纬交织,有时间和空间的交错变幻,有现景和梦境的来回闪烁,有虚实相间的扑朔迷离,甚至有几种文学流派的兼容并蓄,更有多种表现手法和艺术技巧,交汇成诗人饱满酣畅的笔墨,琳琅满目的文境,神乎其技的描绘。布局展示,情节开拓,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由“近”写“远”,由“今”忆“昔”。由此汇成的乡思乡愁的的感情海洋,有心理的微澜,有意识的波涌。一路写来,触景生情,情景相生,情随景迁,移步生莲。文笔挥洒,神思飞越,声色光影,照人心眼,变化万殊,斐然夺目。艺术大观园的故乡榕树,特有的自然美景,最引人观赏。
散文开场,即用对比:有香港现实,有童心浪漫,有榕树理想——在具有特征性的“铅灰色”和“水泥楼房”森林闹市中,开辟一片绿洲,端出一方净土:两棵苍劲榕树,一个儿童乐园。但儿童乐园“此岸”的童心,只是借“彼岸”的理想色彩在描绘;眼前苍劲的榕树,也好像是故乡榕树的幻化和再现。因而散文开头写成的很像是一首明亮的香港“风景诗”——“有两棵苍老蓊郁的榕树,/以广阔的绿荫遮蔽着地面。/在铅灰色的水泥楼房之间,/摇曳赏心悦目的青翠;/在赤日炎炎的夏天,/注一潭诱人的清凉……”原来,诗人是把诗歌写成散文了——因为他的散文就是诗。紧接着散文一段,也是可以“复原”成一首“儿童诗”的,而且是童趣盎然而充满乐趣的:“动了未泯的童心,/卷制成一支小小的哨笛,/吹出单调而醇朴的哨音。/小儿子欢跳着,使劲吹着,/引得一只小黑狗循声跑来,/摇动毛茸茸的尾巴,/抬起乌溜溜的眼睛望他。/哨音停下,小狗失望跑开;/他再吹响,小狗又跑拢来……/逗得小儿子嘻嘻笑,/粉白的脸颊上泛起淡淡的红晕。”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