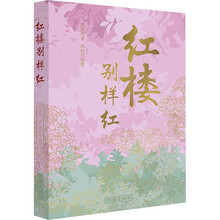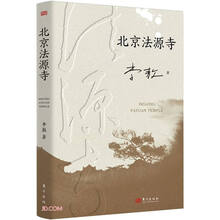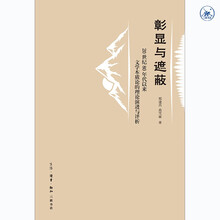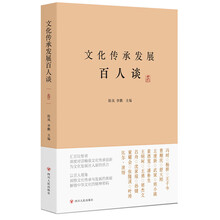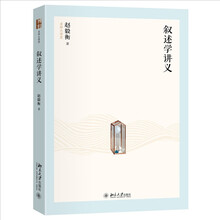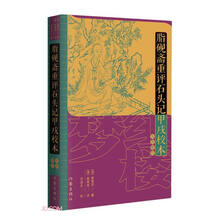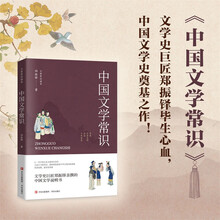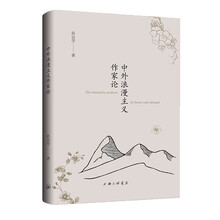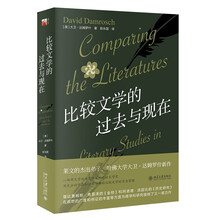《现实的坚守与焦虑:转型期山西文学研究》:
在传统的匡时济世文学观的影响之下,社会学批评家从群体本位的意识形态出发,强调文学的精神向度、社会责任、价值导向,我们当然不能说这种观点是错的。但在当代个性化逐渐成为文学的主体特征时,依然采用这种大一统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进行批评,显然已无法全面公正地进行评判。如认为以美女为代表的女性文学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败坏了社会风气,造成了精神污染,这种批评就有本末倒置之嫌。在美女文本中,吸毒、艾滋病、同性恋等现象的确比比皆是,但这又确实是对当代纷繁复杂、光怪陆离城市生活的原生态反映。何况暴露丑正是为了追求美,正如这些美女是带着真诚走进创作一样。例如棉棉就把写作看作医生的使命,宣称之所以如此写作是因为厌弃自己的过去,并希望以此和过去决裂,引起世人的警醒。《糖》<上海宝贝》《围城男女、》等并不仅仅是把身体当作反抗的武器,也是借用一种无畏无屑的姿态反映问题男孩、问题女孩以及现代人的惶惑、茫然、恐惧、寂寞的心态,这些作品能拥有那么多的读者就说明反映的这种情绪和很多人都有共鸣。如果仅仅着眼于其情绪的表现,只注意到女性意识的泛滥,就难以进入人的精神深层去触摸灵魂的震颤。对一个批评家来说,不仅仅要对文本进行鉴别,还要对文本背后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现象进行分析,这样才能起到批评话语的文化、社会功能。由此看来,今天的批评家对美女作家以至于女性文学责难多于肯定,否弃多于理解,是因为他们仍局限在象牙塔内对社会、文学进行幻想,不愿面对真实的社会状况。单一的批评思维惯性使得批评视角仅停留在对内向性特点的关注,难免会和外向世界产生抵触。
因为批评主体的个体气质、理论文化素养、美学好恶、思维定式等存在差异,所以表现出的审美倾向也会见仁见智。但当下的女性文学批评却都把女性意识的表现作为张扬或否弃的例证,这其实是缺乏一种协调原则、一种宽容理解的态度,并没从作品本身出发去真诚地感受作者创作的初衷,没有感同身受地把握作品的世界,而往往是先人为主,用自己的趣味喜好去左右批评,这样就难以摆脱思维定式的控制、超越自身的偏见,使得女性文学批评与创作运行在平行的轨道上彼此遥遥相望。
女性文学作为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负载着传递社会群众意识的重任,但长期以来,文学批评过分强调性别的差异性,而忽略了文本的多义性,没有去发现和解释女性文学所蕴含的客观意图,这实质上是把女性文学批评从文学批评中独立出来,缩小了女性文学的社会效用。
笔者以为,正如弗莱所讲“作为文学,是不可能讲授或学习的,人们所教所学的只是文学批评”,也就是说文学批评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指导读者阅读,尽量消除读者与文本之间的隔膜,在领略批评家人格精神的过程中,加深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和感悟。只有多层面、多角度地解读作品才能满足不同读者的需求,那么女性文学批评也不应例外。尽管到世纪之交时,妓女作家的出现昭示了女性文学发展的艺术堕落倾向,但它毕竟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无法漠视的现象。既然如此,为何不从反讽的角度去认同它的社会价值,引导读者警醒心中麻痹了的情感,意识到自身的精神危机呢?为何不能通过文学批评达到精神自救的目的,从而真正把批评家的再创造艺术传递给读者呢?当然一味提倡其女性的可贵也并不可取,那样容易导致错误的艺术指向,使女性文学滑向深渊。
由此可见,如果女性文学批评采取截然对立的态度,只会使读者感到无所适从,不知该怎样认识文本价值才更合理,这就从客观上使批评远离了人群,仅仅变成了一种武器和工具,缺乏宽容和同情,也使作品内涵变得狭隘单一。所以我们必须努力改变自己的思维定式,遵循协调原则,多方位去解读女性文学。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