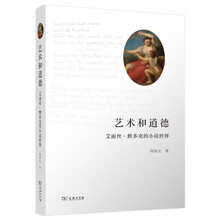说“自以为是” 文/于明诠
我上小学、初中的时候,还不兴考大学。后来到高中要考大学了,只有文理两科,艺体类的特长班在乡下中学是没有条件弄的,因此我就考了师专的政治系。写毛笔字业余爱好而已,更别说画画了。再后来交往了几位画家朋友,看他们涂涂抹抹那样的潇洒,就不免手痒起来。先是比着木版年画描人物,后来嫌不过瘾,就噼噼啪啪地画水墨,有时也看着电视画唱戏的小人儿,再后来就画油画,画陶瓷。在景德镇摆弄那些青花胚胎的时候,特有感觉。双手小心翼翼地捧着,心里就升腾起一种强烈的感觉—不会画画也要画,必须画,而不是写字。可是画什么呢?毕竟从来没画过,那就画小人儿吧,画戏里的小人儿,于是我就乌龙院坐宫击鼓骂曹地折腾开了。
朱新建说,画画是世界上最自以为是的职业,想当画家吗?认真地瞎画就行 。其实,这句话还得看怎样说,这个世界上大凡从事某种职业恐怕绝少能做到“自以为是”的。就说画画,自己面对一张纸的时候,就应该如皇帝一般,管他三宫六院,管他大小三军,都得由着老子随心所欲地折腾。书为心画嘛。谁的心?咱自己的心。可既然是心画,自然天知地知自己知,干吗要画出来?正如民国时期那位钱振煌先生所言,既为心画,那手便是多余,那笔呢?自然更是多余。自己在心里想,哪怕想得天花乱坠做白日梦,甚至杀人放火都没关系,但等到画出来了,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自己看了不高兴撕掉便是。可自己若是看了高兴呢?问题就来了,就憋不住让别人去看。干吗让别人看?想让别人说好。一想让别人说好,一邀宠,就完蛋了,就不能“自以为是”了。重大题材,主旋律,入展获奖,鲜花,掌声,名气,地位,是理事还是主席,每平尺多少钱,等等等等,从此以后就是无穷无尽的“人以为是而自以为非”了,表面上春风得意,但却再也享受不到那帝王般的“自以为是”了。当然,也有人能从这层层包围中“突围”出来,那多是一些非主流的边缘化的艺术家。但这些人有时也是跳出“龙潭”又入“虎口”,因为他们太科班,太技术,太懂画的对错好坏,一句话,他们太会画画了。所以他们想彻底放下那些干扰和约束,享受到真正的“自以为是”,还是不可能。老子问:能婴儿乎?看来是不能,只要智力没有问题,吃五谷杂粮总要长大成熟,总要明白这样那样的道理,咋再倒回去?能在这一层中“突围”出来太难了,简直就是不可能!这是两重“突破”,前一个是突破别人,后一个是突破自己。显然这后一个突破更难。但还是有人就真的成功了,比如说这话的朱新建他自己。在当下所有画家当中,朱新建是第一个,恐怕也是唯一的一个。
所以,我特别羡慕那些从来不会画画儿又煞有介事认认真真地胡画八画的艺术家,而且一心想当那样的艺术家。比如那位“梵高奶奶”,台湾还有一位林渊先生。老先生是台湾南投县地地道道的农民,几乎没念过书,养了一大堆孩子,老伴去世孩子大了他也老了,一个人生活得孤独寂寞。有一天他偶然摸起一块石头,竟像被电击了一样,他说当时仿佛双手捧着一个肉嘟嘟的婴儿,于是他非要把这个可爱的孩子“找”出来不可。怎么找啊,他做过石匠的粗手轻轻摩挲着,他的心里就清清楚楚地看见了,他用锤子凿子剔剜着打磨着,终于出现了,就是那个可爱的小天使!从此他不停地刻呀凿呀,小狗,小猫,小羊,小鱼,应有尽有。家里摆不开就扔到大街上。后来,艺术家们来了,艺术大师也来了,都赞赏林老头是“大艺术家”,是“大师”。老头笑笑,说听不懂。收藏家出天价要买他的作品,他说不卖,喜欢就拉走,正好堆在这里碍事。老头“自以为是”的兴致越来越高,挖来树根树桩搞木刻,用妻子生前留下的毛线在麻袋片上搞刺绣,最有意思的是,用两百多个废旧轮胎堆积起来,他说是“刘伯温”。后来法国的杜布菲,一位现代艺术的执牛耳者,知道了这位“自以为是”胡折腾的台湾农民,多次写信深表敬意。信中说:“ 这些作品展示了作者强烈的创造能力和一种不寻常的力量,更使人感受到不同凡响的新颖及明晰。”其实,林老头中国字都不认得,更别说法国字了,他也根本不知道法国那位杜老头是如何如何的了不起以及他的这些话是个啥意思。他只是“自以为是”地在石头木头上认真地瞎刻瞎画而已。
如此看来,做那些自己压根儿就不懂不会做的事体,极有可能是“横超直入”地进入“自以为是”境界的“捷径”,只因这无知者无畏,就轻松地过了有些人一辈子都难以突破的难关,想想实在划算得很。可是这一“划算”就把艺术教育事业“ 划算”没了。其实呢,光是无知无畏地不懂不会,也是不行的,关键是他心里边要有一种东西,这种东西眼睛可以看不见,但“心”一定要看得见。
当年米开朗基罗就说过:“我要的大卫已经在(石头)里头了,我只是把多余的部分去掉就成了。” 老米一定是闭着眼睛就看见了的,因为睁着眼睛也看不见。看来真正的艺术不仅是睁着眼看,更重要的是会闭着眼睛看。可是,光“心”看得见也还不行,还得有一种强烈地要表现出来的欲望。这种欲望强烈到什么程度呢?不表现出来寝食不安,甚至生不如死。既然到了这个分上,那还等什么呢?
当一个人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去追求和实现一种精神的自由、快乐的时候,就是人生的大解脱、大境界、大快活、大幸福。自以为是—真正做到了,别装,千万不要有一丝一毫的“装”,也许就离那样的境界不远了。
佛像艺术来自印度,为中华民族上升时期的汉唐肠胃消化吸收,有意无意被民族个性增损,历八百载革新为标准国货。作为高峰,还没被有名无名的大师群体所跨越。我国佛像造型妙在在任何角度皆能用一根畅不掩涩的线条勾勒出来,把流变不居的人情归纳为诗性线条按捺进佛脸,你带着什么情绪来古刹巡礼,佛以太极拳式的反弹力加一倍乃至几倍的情感密码电报拍回你的思维,不变应万变,无态生众美。你悲痛则佛示怜悯,你欢欣佛欲咧嘴微笑,你愤之不平佛回赠愠怒,实则表情如故。集对立的审美情绪于一脸,满足人们多种要求。乃壮兄洞悉此中奥妙,收藏多尊古佛造像,朝夕观察,如读禅宗公案,挖出古人以少胜多、以形让意的特殊手段,体现于纸上,揉进时光蚀擦成的斑驳美与金石气息、合理的现代感,浑然一体,揭示圣凡同身、以凡证圣哲的人性化因素。写陶潜、李白、杜甫、苏轼、徐青藤、八大山人、弘一,流露男性博大慈谦的父爱和智慧,又不失人间烟火的活气,形象可信可亲,共性因个性凸出而避开单一、刻板乡愿的平庸。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