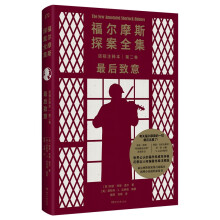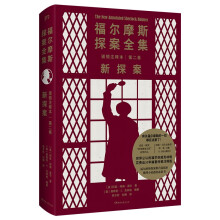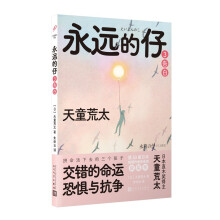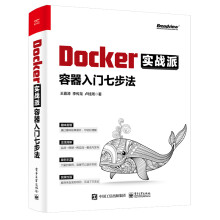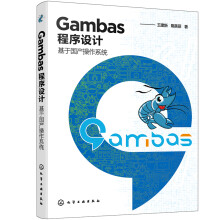《情越千年:中国古典文学简评》:
《诗经·国风》里,关于感情方面的诗占据了绝大多数,而在这些感情诗中,爱情诗的数量又占据了压倒性的地位。相对而言,亲情诗仿佛不那么显眼,仅有的几首兄弟之情、父母之情的诗歌,却又极其撼人心魄。
亲情诗,我认为要数《郑风·扬之水》最为动人。它显然是“思无邪”的又一最佳代表——“扬之水,不流束楚。终鲜兄弟,惟吾与汝。”水流连一束小小的楚木也漂不起来,陌生人的话,就像这水流一样难以信任啊!我们的兄弟本来就少,现在只有我和你了!这毫无疑问是饱经战乱的一双兄弟,在尝尽“谓他人昆,亦莫我闻”的人情冷暖之后所做的感慨。到头来,可以相信的,只有兄弟亲情啊! 这也许是一句和以“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为代表的小清新爱情派相对抗的诗句。那么,亲情与爱情,孰高孰下? 在这之前,我觉得我们最好先看看后世对亲情与爱情的抉择。唐代李华在他的名篇《吊古战场文》中有这样一句话:“谁无兄弟?如足如手;谁无夫妇?如宾如友。”兄弟对于古人来说是如同手足的存在,而妻子不过是“宾友”,客客气气,却难以相亲,便是最亲近的陌生人。关于这种反差,唐代才女李季兰在《八至》中的“至高至明日月,至亲至疏夫妻”最为冷峻,可作辅证一句。
《吊古战场文》中“手足”和“宾友”的强烈对比曾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而刘备的那句“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就更流传甚广了。说难听点,妻子不过是为了传宗接代存在的。在封建礼法的禁锢中,爱情只是可有可无的,并且,最好没有。
相反。在后世,亲情是被拔高在众感情之首的,二十四孝图即可为证。还有什么“姜公大被”之类无法直视的兄弟情故事也被大力宣扬。爱情在后世的被重视程度,与在《诗经》中篇幅的压倒性地位形成了苍凉的对比。
亲情与爱情,在《诗经》中,像是土地与生长在上面的草木。这在《郑风·丰》中得到了具体的体现:“衣锦襞衣,裳锦襞裳。叔兮伯兮,驾予同行”。
女孩儿在亲情的抚育下长大,然后在叔伯的护送下嫁到心爱的男子家,韦庄的《秦妇吟》中“南邻女”出嫁的故事也是佐证。孩子先受到亲情的滋润,成长得美丽而成熟,然后就投入爱情的怀抱。这是一个连续的过程。正如《悲惨世界》里从小无父无母的珂赛特,被冉阿让收养并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物质生活,成长为一个温柔聪慧的贤媛,最终得以凭借出众的美貌和男爵马吕斯相爱并结为伉俪。“这棵凶险的荨麻疼爱并保护了这朵百合花。”若是没有亲情的濡养,爱情恐怕也不会那样完美。
亲情是人类感情生活的基础,而爱情则是升华。
它们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一个硬币的正反面,或是说一种难以磨灭的循环。相爱,结婚,生子,最初的相恋在家长里短岁月静好中缓缓稀释与消磨,打磨得如亲情般丰润而温暖。其实很多执手偕老的爱人,到后来爱情都转化成了亲情。他们的儿女再寻到各自的良人,将这样的循环传递下去。
亲情给予人的慰藉是深沉而温暖的,而爱情则是唯美与陶醉的。像《唐风·绸缪》里的那双乱世夫妇,在一见钟情的狂热下忘乎所以了。而亲情则不会如此。亲情是存在的时候如温火慢热,失去时才会感到 “独行晨晨”的刻骨伤痛。就如脚下的土地,平时熟视无睹,只有在发生地震、泥石流这种毁灭性的灾难时才能感受到;又如鼻梁上的眼镜,只有沾染了尘埃之后才会真切地感觉到它的存在。
所以,“终鲜兄弟,惟吾与汝”与“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并不是相矛盾的。《扬之水》并不是《击鼓》的对立面而是《击鼓》的基础。而《击鼓》也不是《扬之水》的否定而是《扬之水》的升华,这两者相辅相成,就构成了我们人类感情生活最美好的图景。亲情与爱情,就这样在《诗经》中得到了完美的统一。
《诗经》是连接古代与当代的一座无可替代的桥梁。即便是现在,即便是完全与古中国相隔绝的我们,透过这一片片印刷纸和简体字,从这一首首古拙的诗歌里,依然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先人们传达的爱、慈悲与情怀。所以孔子在教导儿子孔鲤学习《诗经》时,才会那样意味深长地说:“小子何莫学夫《诗》? ”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