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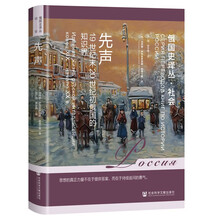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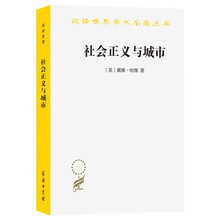


作为中国期刊市场上具有代表性和舆论影响力的杂志之一,《新周刊》年度佳作集结了该杂志过去一年中优秀、有价值的文章,图文并茂,给读者畅快淋漓的阅读体验。
阅读着《新周刊》成长的新锐青年,已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中坚力量。
《新周刊》作为中国社会变迁敏锐的观察者与记录者,记录着中国社会的脉动和中国与世界的互动。阅读着《新周刊》成长的新锐青年,如今已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中坚力量。《新周刊》用敏锐的触觉、畅快淋漓的话语、犀利的评点方式,对时代、社会、城市、生活方式等进行精彩的解读和提炼。
本书包括六神磊磊、张颐武、肖锋等名人对话与访谈,是过去一年名人名篇的集结。它体现着这个时代的情绪心态,将之化为血液的粘度和身体温度,生生不息。
江湖是个什么湖?
文┃谭山山
“我不在江湖,但江湖中有我的传说。”
10月,蛰伏十年的导演田壮壮开始筹备电影《树王》的消息,被媒体解读为“重返江湖”。他用上述这句话概括自己沉寂的这十年,同时自嘲:“我又回江湖了,是吧?这武功全废了回来了。”
江湖传说这句话最早出自导演陈凯歌之口。2005年,《新周刊》采访彼时刚推出电影《无极》的陈凯歌,记者问了陈凯歌一个问题:“如果说电影圈是一个江湖,你觉得自己是哪一个派别?”陈凯歌表示自己没有江湖心,所以并不算一个“在江湖”的人。但是,“就我这样一个不在江湖上的人,江湖有传说。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不能说我人不在江湖,我还是在江湖”。
电影圈当然算是一个江湖,由此类推,互联网是江湖,文学圈是江湖(还记得韩寒说的那句“什么坛到最后都是祭坛,什么圈到最后都是花圈”么),学术圈是江湖,饮食界是江湖,股市是江湖,职场是江湖,各种小圈子也可以视为一个个小江湖……人人都想成为自己江湖的“大侠”。
江湖的多义性
江湖到底是什么?
徐克电影《东方不败之风云再起》中,西班牙人古烈问锦衣卫凌风什么是武林,凌风回答:“武林就是江湖。”古烈追问什么是江湖,凌风不胜其烦,给出一个敷衍的答案:“江湖就是我们武林人士出入的地方。”西班牙人被这个逻辑绕晕了,吐槽道:“你们自己都说不清江湖是什么……”
研究中国游民文化的学者王学泰认为,“江湖”有三重不同的含义。
第一,大自然中的江湖。江、湖并用而成为一个词语,是庄子的贡献。据统计,《庄子》中有七处出现“江湖”,最著名的表述,自然是那句“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九州之内江河纵横,湖泊遍地,因而我们也经常用江湖泛指四方。
第二,文人士大夫的江湖。虽然庄子用的是江、湖的本意,但同时他也给“江湖”赋予了文化美感——一种对精神自由的向往。江湖广阔浩渺,与热闹繁华、名利所在的朝市恰成对立,于是江湖就变成了文人士大夫逃避名利的隐居之所。对他们来说,“江湖”也许在山林,也许在田野,也许在江河湖海,但更多的还是自己早已营造好的小小园林。主动隐遁江湖,是为追寻自由(如陶渊明的“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被动沦落江湖,则是一种无奈(如范仲淹的“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第三,游民的江湖,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认知的江湖。它充满了刀光剑影、阴谋诡计和你死我活的斗争,《水浒传》第二十八回,武松杀嫂后被两名公差押送前往孟州牢城,途中在十字坡遇到黑店老板张青、孙二娘。武松与张青夫妇不打不相识,边喝酒边谈论“江湖上好汉的勾当,却是杀人放火的事”,押送武松的两个公差“惊得呆了,只是下拜”。
王学泰认为,这种“江湖”最早出现在南宋及南宋以后的“水浒”系列和《水浒传》中,“明确地把江湖看成是江湖好汉杀人放火、争夺利益的地方,应该说是始自《水浒传》”。《水浒传》作者施耐庵不仅创造了“江湖”(“水浒”的本意就是江湖)的新概念,还提供了与此相关的一系列话语:“好汉”“聚义”“义气”“逼上梁山”“替天行道”“不义之财,取之无碍”“仗义疏财,扶危济困”“论秤分金银,一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肉”,等等。
所谓“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指的是有人、有共同的文化背景,再加上一套互相认可的行事准则甚至语言系统(“黑话”),就构成了一个场域、一个社会,这就是“江湖”。“市井、乡村、道路湖海都可以是江湖,也都可以不是江湖,关键在于它是不是江湖人活动的场所。”(王学泰语)
也有学者认为,“江湖”就是前近代式(注意,不一定就是前近代时期)家族以外的社会空间,并不专为游民阶层和秘密社会所有,举凡普通百姓,乃至下层士大夫、知识分子,都或多或少要涉身“江湖”。
作家阿城在短篇小说《江湖》里写到这样一个情节:重孙子给已经九十多岁的孙成久读台湾、香港的武侠小说,读得多了,就说自己想做个江湖上的英雄。孙成久回答:“武侠里有个屁的江湖。早年听人念说《红楼梦》,里面有个凤姐,就是在个王府里,倒是懂江湖的,算得上是个江湖英雄吧。江湖是什么?江湖是人情世故,能应对就不易,更别说什么懂全了。打?那是土匪。”
江湖是一种方法论
借鉴日本历史学家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的说法,我们可以说,“江湖”是一种方法论。
南京大学教授李恭忠认为,“江湖”作为一个独特的视窗,在中西学者熟悉的“儒教中国”“帝制中国”“乡土中国”等局部意象之外,提供了一个关于传统中国的整合性框架,即“江湖中国”。
李恭忠对江湖的定义是:“江湖”是熟人社会以外非熟人、非透明、乏规则的互动空间。首先,在江湖这一跨乡土层面的人际互动空间里,形形色色的行为主体相互交叉、汇集,组成了一个陌生人的世界——这就是“非熟人”;其次,交往主体彼此并不熟识,相互之间展现的只是一个有限的侧面,甚至有意以“假面”示人,掩饰了真实身份、真实意图——这就是“非透明”;再次,在这种开放的、流动的交互空间里,虽然遵循“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基本原则,但对于“利”,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理解。在缺乏统一、清晰、制度化的基本规则以及维护这套基本规则的体制性力量的情况下,不同层次或不同主体的“利害”冲突,很容易走向你死我活的竞争和对抗,最终只能诉诸最原始的手段——暴力——这就是“乏规则”。
在李恭忠看来,“江湖”不仅仅是中国人所身处的瞬时性社会互动空间,在历史的变迁过程中,它还积淀为一种历时性的文化传统,超越了单一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可以跨越时空环境而传承、传播,并且反复得到“激活”。
这就是“侠客梦”能打动一代又一代人的原因。江湖的最大魅力就是挑战秩序,张扬人性,江湖中人也就是侠客(或曰游侠,或曰好汉)经过评书、传奇、武侠小说乃至影视剧的演绎和渲染,成为自由、浪漫、仁义、慷慨、潇洒的化身。只要你不满平庸的生活,追求不平凡的人生或更有意义的生活,你就会对江湖那个自由的世界心向往之。
作家绿妖把短篇小说《硬蛹》的背景设置在上世纪90年代的北方小城。少女黄玲玲每天半夜用自己的土办法练轻功,在她看来,“武功是另一个世界,它是画在现实世界上的虚空的辅助线,它是无限。靠我们的智慧无法理解,只能相信”。与其说她想成为武林高手,还不如说她想借助练功,暂时脱离苦闷的现实世界。
侠之终结
“你想想,就算你报了这个仇,那之后呢?就算法律没找到你,也是一样,那之后呢?这个年代,你一身武艺又上哪儿去施展?现在连你们的镖行都没有了,你还能干什么?天桥卖技?去给遗老做护院?给新贵做打手?……跟我们去美国走一走吧,出去看看世界……我告诉你,这个世界很大,大过你们武林,大过你们中国……去看看,这不也是你们老说的跑江湖吗?”
在张北海的小说《侠隐》中,马凯医生救了在灭门惨案中幸存的李天然,并劝他放下那套“有恩报恩,有仇报仇”的江湖规矩,离开中国,去看看世界。“侠隐”里的“隐”,一方面指像李天然这样的侠士“大隐隐于市”,一方面也可以解读为“侠之终结”。
“侠之终结”是必然的,因为时代变了,“枪炮取代了弓箭,法律取代了道德正义”(张北海语)。所以在小说中,蓝青峰感慨道:“我都不敢相信今天还有你们这种人……你大概是最后一批了……”
著有《江湖中国》的学者于阳认为,江湖社会并非农业宗族社会,更不是现代法治社会,这种看上去“不古不今”的社会,是古典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的过渡产物。写有《江湖,中国社会的真相》一文的学者蔡永飞更进一步,认为“江湖观念不利于社会的发展进步,不利于建立一个健康的良性运行的社会秩序,是中国文化中的最大糟粕之一”。
“任何社会的发展进步都必须以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为前提,都必须建立有合作有竞争的规范秩序,我们要发展的市场经济更是一种规则经济、法制经济,因为市场经济要求人们在经济生活中进行最广泛深入的交往,并在交往中形成最广大的人群的共同利益所需要的、所有的人都必须遵守的规则,它和江湖观念、江湖方式无疑是尖锐对立的。”蔡永飞写道。
张北海也说,“侠”也要走向现代化。小说里的李天然虽然不是出于自觉,但他还是学会了使用手枪这一现代武器,而不是靠拳头解决问题。“西方创作早已将这类故事人物带入20世纪,我觉得中国不能永远生存在一个遥远的过去,一个虚无缥缈的世界。应该有人设法将‘侠’置放在现代社会。”张北海说道。
心有猛虎,细嗅蔷薇。江湖已经远去,现代社会需要现代的“侠”。
《新周刊》是一所学校,他培养了很多人,他的精神在很多地方发扬光大。
央视主持人 白岩松
在我心里,《新周刊》就是中国的《Time》。
学者 于丹
我一直觉得《新周刊》就是一个小孩的形象,他童言无忌,他永葆好奇。他会追问为什么,他会在大家都对某些规则习惯于隐忍和忽视的时候,他突然说那个皇帝好像没穿衣服。
资深媒体人 杨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