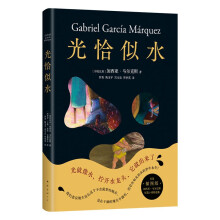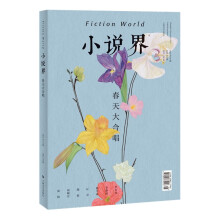《且听风吟(新版)》:
说起来话长,我现已二十一岁。
年轻固然十分年轻,但毕竟今非昔比。倘若对此不满,势必只能在星期日早晨从纽约帝国大厦的天台上跳将下去。
以前从一部世界经济危机题材的电影里听到这样一句笑话:
“喂,我从纽约帝国大厦下面路过时经常撑一把伞,因为上面总是噼里啪啦地往下掉人。”
我二十一,至少眼下还没有寻死的念头。在此之前我同三个女孩睡过觉。
第一个女孩是高中同学。我们都十七岁,都深信相互爱着对方。在暮色苍茫的草丛中,她脱下褐色无带鞋,脱下白色棉织袜,脱下浅绿色泡泡纱连衣裙,脱下显然尺寸不合适的式样奇特的三角裤,略一迟疑后把手表也摘了。随即我们在周日版的《朝日新闻》上面抱在一起。
高中毕业没过几个月我们便一下子分道扬镳了。理由已经忘了——是那种可以忘掉的理由。那以后一次也没见过。睡不着觉的夜晚有时想起她,仅此而已。
第二个是在地铁车站里碰见的嬉皮士女孩。年方十六,身无分文,连个栖身之处也没有,而且几乎没有乳房可言,但一对眼睛满漂亮,头脑也似乎很聪明。那是新宿暴发声势最为浩大的示威游行的夜晚,无论电车还是汽车,一律彻底瘫痪。
“在这种地方游来逛去,小心给人拉走哟!”我对她说。她蹲在已经关门的检票口里,翻看从垃圾箱里拾来的报纸。
“可警察会给我饭吃。”
“要吃苦头的!”
“习惯了。”
我点燃香烟,也给她一支。由于催泪弹的关系,眼睛一跳一跳地作痛。“没吃吧?”
“从早上。”
“喂,给你吃点东西。反正出去吧!”
“为什么给我东西吃?”
“这——”我也不知为什么,但还是把她拖出检票口,沿着已无人影的街道走到目白。
这个绝对寡言少语的少女在我的宿舍住了大约一个星期。她每天睡过中午才醒,吃完饭便吸烟,呆呆地看书,看电视,时而同我进行索然无味的性交。她唯一的持有物是个白帆布包,里边装有质地厚些的风衣、两件T恤、一条牛仔裤、三条脏乎乎的内裤和一包卫生棉条。
“从哪儿来的?”有一次我问她。
“你不知道的地方。”如此言毕,便再不肯开口。
一天我从自选商场抱着食品袋回来时,她已不见了,那个白帆布包也没有了。此外还少了几样东西:桌上扔着的一点零钞、一条香烟,以及我的刚刚洗过的T恤。桌上放着一张留言条模样的从笔记本撕下的纸条,上面只写着一句话:“讨厌的家伙。”想必指我。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