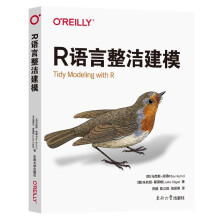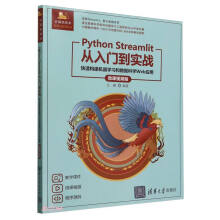我的上海时代(1932年底至1938年底)整整六年。在回忆上海时代的时候,首先第一个感觉是,这六年是我人生的一个亮点。不仅是一个亮点,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以后的人生。<br> 我所经历的这一时代,正是当时中国历史、日本历史以及世界历史上动荡不安的时代,发生了西安事变以及其他各种事件。在这六年中所接触到的,和亲聆教诲的前辈友人也为数不少。<br> 当我作为“联合通讯”(完整地说应该是“社团法人新闻联合社”)上海支局长去上海赴任时,只是一介普通的新闻记者,突然被卷入了各种重大事件中,不分朝夕地处理每一个突发事件的新闻或流言。在这过程中逐渐开阔眼界,学会了把握审视复杂动荡的形势。当然,作为一个日本记者,我对于形势的理解是有限的,我的回忆也并不是学术性的总结。但是,在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充分的情况下,我的回忆也许能成为研究的资料,这种想法在我脑中浮现过好几次。同时,也担心虽然是实际经历过那段历史,但个人的记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淡忘。<br> 中央公论社在几年前热心地鼓励我出版回忆录。但我觉得写自己的事太狂妄自大,而且还有可能得罪一些人,所以几度犹豫。可连我的畏友冈毅武也再三来劝我,说“写回忆录是你的责任,也是义务。不管什么事都放下,先把回忆录写出来”。我不觉得我的回忆的价值像冈君所说的那样,但国内外友人都劝我把它写出来。我还是很难决定,但想到能够叙说良师益友的事情,而且如果能把我在当地感受到的当时的情景从我的视点来描述,或许能提供一些参考,终于决定执笔书写。<br> 这里我想介绍一下我作为记者在去上海以前的经历。在这里叙述我个人的私事很感到惶恐,但是我必须讲述一下把我派往上海的岩永裕吉的事,同时还有我和岩永裕吉相识的京都太平洋会议,以及带我们去京都太平洋会议的恩师、美国研究学者高木八尺先生。还要叙说把高木先生介绍给我的黑木三次。我在美国留学期间,我的父亲松藏教导我尽量和中国留学生交朋友,比尔德博士告诉我中国问题是日美关系的核心,蜡山政道教我国际政治,嘉治隆一鼓励我写时政评论,这些我都必须涉及。<br> 去上海的经历写得稍微长了一些,但这些都是在我的人生中给了我很大影响的前辈,因此这既是我去上海前的经历,也是我整个回忆录的前期经历。<br> 1.留学以前<br> 我考进东京帝国大学是1920年(大正五年)9月,毕业是在1923年3月,大学的讲义中最感兴趣的是末弘严太郎先生的民法,和高柳贤三先生用英语讲授的法哲学史(当时不叫法哲学,叫法理学)。毕业的时候,刚开始读英语的《资本论》,只觉得正义感受到刺激,并没有意识到其中提出的尖锐问题。当时的想法只是不去贪图官禄,也不想去银行大公司,把自由职业或自由作家当作自己将来的方向。我希望能当上律师,或新闻记者,或者大学讲师,为此我要求父亲让我继续读书,进了研究生院。<br> 要成为研究生院的研究生,在形式上必须确定专攻科目和指导教授。我决定专攻法理学,当时法理学专业有笕克彦和穗积重远两位教授,在当时这个专业被称作竞争科目。笕先生著有《西洋哲理》和《佛教哲理》两本大部卷著作,在本科生时期也听过笕先生讲课,但是我不想搞神道之类的,虽说指导教师只是一个形式,我还是请穗积先生指导。当时研究生的生活很自由,没有请穗积先生指教过,甚至研究生期间一次也没见过他。几年后我成为东京大学的助教,我对穗积先生说:“那时我真是太失礼了。”穗积先生却说:“没关系。”末弘先生比较熟悉,在本科生的时候,有时晚上和同学一起到他家,听他谈论。考上研究生以后,一次在法学部研究室前正好碰到末弘先生,我向他致意,末弘先生说:“法学部研究室给你另加桌椅,以后就在这里学习吧。”其实不是一个房间,而是像过道一样的地方放上了桌椅,以后我就每天在这里读书。记得当时读了《资本论》,还有恩格斯、河上肇的著作,也读了佐野学的《俄国经济史》等。<br> 那时,教授们都去山上御殿,那里有一家名叫“钵木”的西式餐厅,在那里吃饭。副教授和助教都在法学部研究室的一个大房间里吃自己带的盒饭。末弘先生对我说:“你虽然没有资格,但我已经和各位先生说好了,就一起吃午饭吧。蜡山政道、我妻荣、木村龟二、平野义太郎他们都在,都是读书很用功的人,一起吃饭对你的研究有帮助。”于是我就忝列这些学者之后,每天中午和副教授、助教一起吃饭。然而,副教授和助教们谁都没有时间和我这个新来的研究生慢慢地说话,都伏在自己的大书桌上,书桌的前面和两边都堆满了书,大家都埋头啃书。吃饭最快的是蜡山政道,不到十分钟就吃好了,接着马上又开始继续看书。吃饭时副教授和助教偶尔稍微交谈几句,这时我就竖起耳朵听,不漏过只言片语。不管怎么说,在放暑假前的四个月是非常愉快的。P1-3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