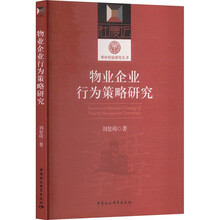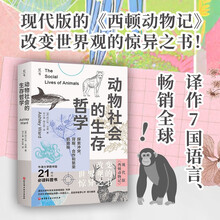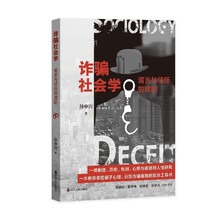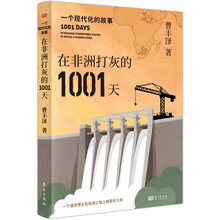1.两个“郑卫宁”
问:我一直把您看作两个不同的人,一个是我面前的、真实的郑卫宁,一个是灵性的、作为精神的郑卫宁,您自己怎么看?
答:我觉得你说得特别深刻。我常常回忆,自己小时候正逢“文化大革命”,书籍很有限,我又没上过学,所以抓着什么读什么。当时法国雕塑家罗丹雕的巴尔扎克给我内心的震撼很大,那是对巴尔扎克破烂不堪的肉体和隐藏在那个躯壳里面的精神的一种颤动,所以说,你说到我心里去了。
问:您是在什么时候觉得有两个不同的“郑卫宁”?
答:我从小患先天血友病,生下来就不能走路,13岁之前,又接触不到辅具,就那么在地上爬,一生也没进过校门,这是很让人自卑的。再加上自己的身体,每天就是出血、输血、抢救,这样的一个身体,肯定是不会被自己的精神认可的,所以说就我这样的特殊情况来讲,可能很早就有这样的感觉。
问:您十几岁的时候就有?
答:对。
问:您实际上意识到了有一种分裂?
答:对。我跟所有的媒体都没有谈到自己的童年。而实际上,我自己的成长过程、我的童年对我这一生的影响非常大。但我们这个群体有很多是比较弱的,比如残障社工是提供社会服务的,他需要有非常强大的思想和心灵才能做好心理咨询,才能做好社工的工作。但我们在培养残障社工的时候,最开始是感性的发现,发现残疾人特别弱,不像在设计软件和动漫方面,他比健全人强,通过电脑屏幕,他只要有耐心很快就会超过健全人。残疾人做社会服务工作就是不行,即便在我们这么着力培养的情况下,即便背后有几千个大学生残疾人团队的支撑,我们11个社会组织的残障社工也占不了整个社工比例的20%。溯根求源,因为从小残疾以后,家庭不论贫富,一定对他呵护有加,这个是很大的问题。
在中国过去的老式家庭里,一般的男孩女孩其童年的成长很被忽视,要不就给挂个钥匙,要不就让隔代的老人带,然后有啥就吃点啥,都是跟着老人过日子,都是自己管自己。所以他们到大学毕业以后的家庭生活、宿舍生活、组织生活、形成的人格和残疾人是完全不同的。残疾人的心灵从小就被呵护,他跟主流社会那些心灵强大的人缺少交流,也没参与过广泛的社会竞争,他有很大的自我。像我们说的心中有个大大的我,做什么事都要关注外界怎么看自己,自己会怎么样,不像一般的主流社会的青年们,到哪儿求职到哪儿打拼,进去就是拼,没有想到自我的那套东西。
问:在精神上,您跟他们不同?
答:是的。我自己有这样一个体会,我在精神上不认同我是血友病群体的一员。比如我到各地去,都不参加血友病患者的聚会。血友病患者有五十多岁、六十多岁的,也有十几岁的,他们的聚会我不参加。我根本就不认同我是他们当中的一员。血友病患者是残疾人这个人群当中最孱弱的群体。举个例子,你去参加他的聚会,如果是个长沙发,你坐下来的话,他就说,慢一点别碰到他,因为他一碰就出血,旁边坐一个人,他都害怕无意当中会碰到他的胳膊和腿。他们的精神状况也非常的弱,觉得能维持着不出血就行,走到哪儿都不敢动,哪像我拄一跟拐棍全国各地到处跑,这种精神状态完全不同。所以血友病患者的聚会我不去,但我可以赞助。七年前在深圳开血友病大会的时候,我从国外的血友病组织那里要了三大箱药,通过海关进来。大会上有几百个人,我给每个人发了六瓶,一千多块钱一瓶。即便我全自费,我也愿意去帮助他们,但是我不去开这个会,我不愿意跟他们坐在一起。从他们的家属到他们本人,弥漫的那种悲观,那种保护的气氛是不行的。
2.少年回忆
问:您童年正逢“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对您人生的影响大吗?它与您的这种分裂是否有联系?
答:别人看起来“文化大革命”给我带来的影响是灾难性的,让我一天学都没有上过,但我特别感恩“文化大革命”。仔细回忆,可能造就我这一生这样的性格,主要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也就七八岁,但是“文化大革命”对我来说记忆犹新,我觉得主要原因是我们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时我的父母都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我母亲是地方的局级,而我的父亲是军级,他是部队里的将军,但他是在一个院校里,就是现在的武汉海军工程大学,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个院校属于“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批判)单位。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