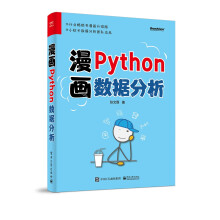第二位当属于光远。作为后学,邓伟志说道:“我在学术上无法同于老相比,可是,我在学术上同于老又有些相像之处。在我的学术生涯中,受于老的影响太大了。”欲问“影响”何处?即“抓住真理,所向披靡”、“勤奋好学,笔耕不辍”。邓伟志举出一例:于光远“嗜书如命”,为了借一本书读读,费尽心机。他读书破万卷,是标准的“采了百花再酿蜜”。在他身上读与写的比例是百比一、千比一。邓伟志说,从他的“读写比”始知什么叫理论深度和高度。深度不是自吹的,只有把头埋在书堆里,才能深;高度也不是捧出来的,只能是站在一位又一位学术高人的肩上,做到像杂技的“叠罗汉”那样,才能高。
至于第三位,邓伟志说就是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后任安徽省委书记的曾希圣,他的特点是“敢说真话”,“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那年,邓伟志他们跟随曾希圣到奉贤县胡桥公社孙桥大队搞“四清”,曾希圣化名“余勉”,公开身份是华东政法学院教授。在孙桥,“余教授”和司机两人住在两间加起来不超过20平方米的茅屋里。可是,白天在屋里找不到他;晚上,屋里又常常坐满了人。不管刮风下雨,他都喜欢往外跑。孙桥大队共有15个生产队,男女老少都认识“余教授”。按照上级吩咐,“余教授”出去要有人陪同、照顾。但“余教授”很喜欢甩掉陪同人员单独走出去,看饲养场、电灌站、自留地,找干部、社员谈话。当警卫员向他提意见时,他笑着回答:“到了孙桥,你们都是工作队员……”他单独跑生产队,可以说是“随机抽样”,他说:“不要以为住到了队里就是深入了。深入是过程,是学问。”说起来,邓伟志有过亲身经历:邓伟志有段时间兼任他的誊写员,一次曾希圣要他写阶级阶层状况的调查报告,邓伟志写了交曾希圣修改。曾希圣修改后,邓伟志再誊写清楚。正誊时,一位复旦大学的女队员来大队部送材料。她问邓伟志在干什么,邓伟志说誊写曾老的修改稿。她问:“曾老的文字水平怎么样?”邓伟志自不量力地给她吹开了:“这份报告中,‘曾中有邓,邓中有曾’,我已誊得差不多了。你能有本事看出哪些是我写的,哪些是曾老加上去的吗?”她接过去辨别,不一会,她指着其中一句说:“这一句很深刻,你写不出。”邓伟志凑过去一看,果然是曾希圣写的:“这是辩证法加给我们的困难。”邓伟志想,这般富有哲理的句子,确实不是我邓某这号人所能写得出的。在理解了这句话的分量后,几十年来,邓伟志不知把曾希圣的这一警句引用过多少次!
“学术之路并非是平坦大道”
邓伟志是我国第三代社会学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持续几十年对社会稳定和发展问题进行不懈而深入的研究。若要划分的话,邓伟志的学术生涯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1960年至1976年前后,是他研究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阶段,以自然科学为主;1976年前后至20世纪末,主要从事家庭社会学、妇女学和知识社会学的研究;2000年至今,主要集中在政治社会学领域。不过,邓伟志说:“在社会学上,我不是科班出身,社会学下有170多个分支学科,我只不过进了两三个分支的边门”;他冷静而幽默地评价自己,若把22卷的全集各卷加在一起,“其总和还够不上社会学分支学科数的一个零头。媒体上称我‘社会学家’,我实不敢当,充其量我是‘家’字下面那个‘豕’身上的一根毛。”这并非自谦,20世纪60年代,邓伟志学的是政治经济学,他的学术理想是按前辈学者、领导的培养目标当一名“冲锋枪”式的杂家,但“文革”的爆发,改变了邓伟志的人生命运,准确地说,这场“革命”,使邓伟志经受困惑、磨难、厄运,更多地学会独立思考、敏锐观察,出现“遵命文学”转向“自觉文学”的人生拐点,也决定了他的学术之路不是一条平坦大道,而是充满荆棘的崎岖山路。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