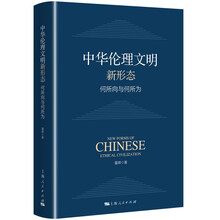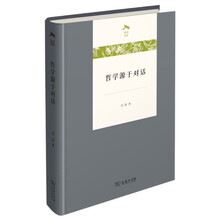在对个别要素的估量中,哲人的个体能力与经验,他的时代诊断、他对哲学处境及其与哲学传统之关系的评估,都具有重要性。所以,在政治迫害极为严重的时代,位于学说中心的自然是对哲学的政治辩护,而非理性的奠基。另一方面,政治辩护所采用的修辞也因情形而异,鉴于——当前现实的或将来可能的——组织良好的共同体所采用的修辞,显然会不同于顾及一个没落的、非常成问题的社会所采用的修辞。政治辩护在面对哲学的强大敌人或坚决质疑者时的遭遇,会不同于对哲学的诉求成为时尚之时。在前一种情况中,辩护会突出强调哲学有益的政治影响和巨大的社会用处,或至少会声称哲学的相容性和安全性,在后一种情况中,辩护更多地会强调对立,突出根本的区别,着重指出哲学对于奠基的需求,以防止哲学被收编,变得没有方向和浅薄化。
自苏格拉底转向以来,政治哲学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我们同样可以从中见出这种现象的多元性。我们看到,亚里士多德首先尝试,从哲学出发将政治事物归为一个自足的知识领域。他既以柏拉图对政治哲学的奠基为前提又与之相脱离,他将一门可教可学、可以被公民掌握的政治科学独立出来,由此能够赢得未来的政治家作为哲学的同盟,而且将哲学生活对于政治生活的严格凌驾提升为政治一哲学学说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凌驾还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传统中的不言而喻之物。我们穿上历史的七里靴,从这次卓越的友爱政治行动直接跨越到马基雅维里的大胆之举,他通过对哲学的一种极端政治化来重新赢取libertasphilosophandi[哲思的自由]。他也试图赢得一门实践科学作为自己的同盟。他所谋求的与主权者——君主或者民众——的联合当通过政治与神学的有效分离持久地保护哲学的安全。他是如此一贯地用精神战争的要求来统摄他的政治哲学陈述,以至于他不仅抛弃或避免了哲学传统中所有能够为对手提供出发点或者能够使未来哲人柔弱化的概念、术语和理论,而且甚至还不把全部行动的目标,即哲学生活本身明确地作为论题。然而,如果从马基雅维里专注于政治事物的认识和对这种认识的政治陈述而得出结论,认为实事的另外两重规定。对于他的政治哲学是没有意义的,那就错了。同样的情形也适用于阿尔法拉比和迈蒙尼德的政治哲学,他们分别在马基雅维里之前六百和四百年对启示宗教的挑战做出了回应。当他们把启示信仰的基础置于中心的时候,他们考虑到了哲学处境的变化。他们把神法、神意和先知作为政治事物来理解,这是接续了柏拉图式的政治哲学。当阿尔法拉比和迈蒙尼德着眼于“完美城邦”的奠基而作为奠基者和立法者为律法奠定哲学基础的时候,他们所依循的也绝不只是政治意图。因为他们正要在为律法奠定哲学基础的时候,极其尖锐地提出哲学生活的权利问题,而哲学的理性奠基也一同在其中成为议题。
马基雅维里及其追随者所发起的与政治主权者一道有计划地征服自然、理性地重新安排社会秩序所引发的历史剧变,深刻地改变了哲学的处境。政治从神学的解放[35]成功地释放出一个日益目的理性化、不断繁荣的世界,而这最终导向了政治要求同宗教要求一样被不加疑问地拒斥。随着一次旨在巩固和平与安全的行动,哲学失去了最严肃的对峙所必需的严苛的替代者。哲学的轮廓渐渐模糊于纯粹私人事物之杂多,在这当中,一切看起来都与一切相容。于是,政治哲学就面临着这样的问题,即哲学的逾越和上升在这种条件下是否比以前都更需要预先进行一种反向奠基(Gegen—Gmndung),这种奠基的发起者是哲人自己,它重新让人意识到政治事物的品级,看到政治生活的尊严,并就那些最合适的人选对于现存关系的不满足而予以新的方向,将他们引向哲学。在此意义上,哲人如卢梭、黑格尔和尼采在18和19世纪用相反的政治计划来回应他们所看到的那个过程,即“市民”或“末人”的到来和占据主导。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