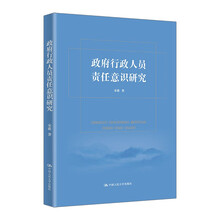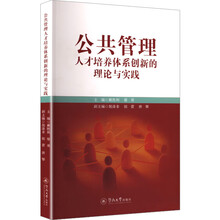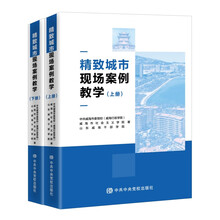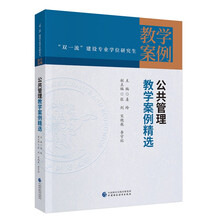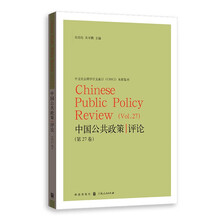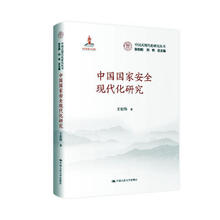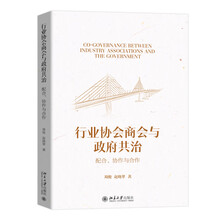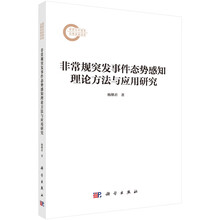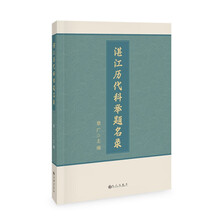规范行为。一个社会组织的出现必须先有各种规章制度,一旦加入了该社会组织成为其会员,就必须要遵守组织内的规章制度。我们的社会管理要管理人的行为,社会组织便可以在其组织内对它的会员进行管理。
表达诉求。社会组织中有很多的社会成员,当这些成员的权益受到损害的时候,通过所在的社会组织来向政府反映情况,由社会组织与政府通过谈判、协商的方式来维护成员权益,表达成员的诉求。
有效监督。社会组织可以监督企业是不是按照要求生产合格的产品。比如消费者协会,每年都会在“3·15”把监督的情况发布出来,督促企业做合格的产品,履行社会责任。社会组织还可以监督政府,监督官员,督促官员和政府公平地制定政策,更好地履行政府的职能。
记者:《决定》中允许几类社会组织在成立时可以直接依法申请登记,不必经过政府主管部门的审批。这么做的话,会不会产生一些潜在的问题?
向春玲:针对社会组织我们有着各种各样的管理条例,比如社会组织在符合什么条件下才可以登记,我们民政部门还对他们有着一定的考评考核机制以及相应的管理的措施。社会组织管理条例主要有三种:社团组织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的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组织的登记管理条例。因为中国的社会组织主要是三大类,社团组织、基金会组织和民办非企业组织。当然在广义上,还有人民团体、城乡社区这些组织,它们都是属于在政府和市场之外的,有法律和相关的行政制度去管理它们。一旦出问题,有关部门就会进行处罚,严重者即会将其取缔。十八大之后,政府对社会组织的管理体制有了重大的突破,由原来的政府主管部门和民政登记部门的双重管理向直接登记转变。即一些为经济社会服务的社会组织,例如行业协会、科技类、公益服务类还有城乡社区组织等不用政府业务主管部门的审批可以直接在民政部门登记,但是,对于政治类、法律类、宗教类和一些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代表机构,由于情况比较复杂,政府仍然实行双重登记。
记者:去限制这些社会团体的条例法规算不算是社会强制呢?社会强制与社会共治该如何结合?
向春玲:我不使用社会强制这样的概念。人和社会组织都要按照一定的法律法规来办事,一旦有违背,肯定有相关的法律法规来进行管理。其实,现在社会组织有很多类型,有服务类的、学会类的、商业类、法律类的、环保类的等。国家对社会组织的管理采取了这样一些办法,以往对社会组织的传统管理方式是双重管理,表现为一个社会组织要登记之前必须找到政府业务主管部门,有了政府主管部门审批之后,才能在民政部门登记。而我们这次提出“社会治理创新”中,很重要的一层含义就是激发社会的活力,那么就不能对社会组织进行僵化的强制性的管理,要让那些为经济社会服务的社会组织发展起来。
政府好多的公共事务自己做不了、也做不好,需要社会组织去做,这就要求政府简政放权,还权于社会。就如同当年我们经济方面的很多事情,光靠国有企业是不能完成的,必须要民营企业、个体企业的广泛参与。现在我们对社会组织的管理已经突破了双重管理体制,就是要激发社会的活力。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中用了一句话:“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就我的理解,就是要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特别是为经济社会服务的社会组织,我们要大力的发展和培育。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支持和发展志愿服务组织。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成立时直接依法申请登记”。就是说对于行业协会,慈善服务类、科技类的社会组织,还有就是城乡社区组织四大类社会组织我们已经不需要业务主管部门审批了,降低了登记的门槛,只要符合登记条件,就直接由民政部门登记。我刚刚从广东参加全国社会体制改革论坛回来,广东省放宽的幅度则更大,大概是八类社会组织可以直接登记,简化程序。政府为多数社会组织的登记和成立,提供大量的、好的发展空间。当然,对于那些政治类的、法律类的、宗教类的和境外的一些非政府组织在华代表机构,这些比较复杂的社会组织,我们仍然坚持双重管理,成立这些社会组织,在申请登记前,仍需要经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我觉得“社会强制”的概念可能是指对这些组织的管理,但也不能称之为“强制”。因为只要这些组织符合条件,我们仍要给它登记,仍然要帮助它发展。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