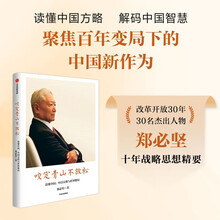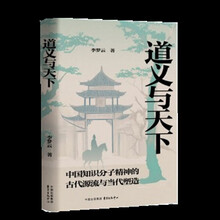第二点是模仿美国独立纪念日及法国革命纪念日这个面向。废除了君主制的中华民国,在当时世界仍属少有的共和国。因此,美国及法国在种种层面中皆成效法对象,在某种意义上是自然而然的结果。这与辛亥革命专被定位为“共和”相对于“专制”之胜利,而非“排满”之成功这点,应该也有关系。此外,清末梁启超所介绍的关于“祝典”的观点——庆祝事业功绩成功而非君主诞辰——既已普及,加上最大的效法对象不外乎美国独立纪念日、法国革命纪念日这样一种认知,使得效法美、法的国庆日制定及实施更加顺利。
不过,自起义以来战斗激烈的武昌,值此第一届国庆日之际,在追悼烈士的同时,大规模地进行伤残军人的游行和勋章、恩赏的授予,追悼的面向特别受到强调⑦。因此,这样一个仿照美国独立纪念日、法国革命纪念日的共和“祝典”之面向,可说是在民国成立之际没有发生实际战斗的地区特别受到重视的要素。
第三点是国民参与的面向。国庆日仪式中演剧、运动会,以及游行或展示革命纪念品等筹划,皆具有与近代国民形成相系的教化意图,具备通过令国民广泛参加,使“爱国”“文明”“共和”“尚武”等价值内化的启蒙性“娱乐”的面向。
第四点是纪念日与历法的关系,这是与全国同时举行纪念活动相关的问题。从临时参议院中的讨论可知,中华民国纪念日必须是阳历这个认知在政府方面已无疑是共识。但在当时的社会中,阴历的使用是当然之事,对阳历则尚不习惯。例如当时以民国初年国庆日为主题的《逛天坛》这首民俗歌谣,就有“九月初一举办纪念会追祭死亡烈士前”的歌词(1912年10月10日为阴历九月一日)①。只是,日后吴稚晖所创造的词汇“双十节”作为国庆日的通称受到广泛使用,这对“国庆日即十月十日”之印象的深植应有相当程度贡献。
关于日后北京政府时期如何举行国庆日,姜瑞学及李学智的论文所述甚详②。两人指出,由于1915年国庆日活动遭袁世凯中止,使得帝制失败后翌年即1916年国庆日作为“共和”复活的纪念呈现空前的热烈盛况,而且在张勋复辟事件后的1917年国庆日活动,也同样在标榜、称扬“共和”之名下举行,这正与本章的第二项结论相关。此外,他们的研究也指出国庆日是社会各界休息和娱乐的时间。
不过,李学智指出民国初年的国庆日活动的特征是“在官方的主持、组织下进行的,各界民众积极参与”的“官民同庆”,而后来官方活动逐渐局限于阅兵或叙勋、宴会,民众则独自进行集会、演说、行进等活动,形成一种分离现象。特别就1920年代而言,国庆日的活动成为民众对政府表达批判之空间的这项指摘甚为重要。然而,如本章所见,北京政府关于国庆日民众活动除了悬挂国旗以外并无法令的规定,而且在民国初年的时间点上,政府的纪念活动已限于形式上派遣代表出席追悼仪式、阅兵、叙勋、宴会等,共和纪念会从经费和人员两方面而言皆属政府外部组织。如此,不如说政府外部的知识分子和社会团体主导的活动自始即与政府活动分离这点,才应视作北京政府时期纪念日活动的特征。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