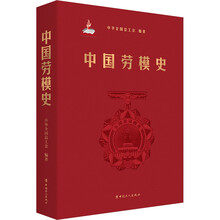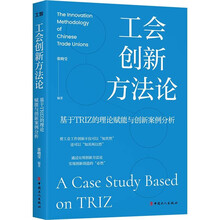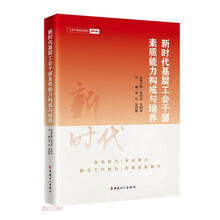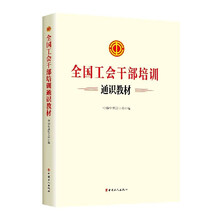《农民城市化遭遇国家城市化》:
这些传说与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中关于拉扎克和哈吉·布鲁姆的故事异曲同工,笔者认为同样可以理解为一种“宣传攻势”,在北坞村每个村民都可以观察到与他们最接近的村官的行为,通过对于他们故事的添油加醋、修饰加工的描述,获得一种权力的象征性平衡(詹姆斯·斯科特,2007)。关于村官们的传说在下文中也会不断出现,笔者没有接触到玉泉北坞村的基层干部,所以这些流言和他们的态度无从考证。笔者认为这种流言的传播多是出于农民对于不可挑战的权力和潜在的不公正的抵制方式之一,但这只是部分农民所选择的一种行为策略。
黄大妈说自己家现在就靠每月租房的4000元钱生活,上面又没什么人,顶梁柱不硬,所以也没什么其他的办法。如果要真去进行上访之类的,上面又没有人,最后倒霉的很可能还是自己。所以也只能不搬,就在这耗着。想要几百万那是不现实的,但是就像马路边那家就是不搬,那他们也没办法。现在还有人家没量呢,而且大多数都还没签字呢,肯定得拖着。在聊天过程中,姜大爷出去遛弯回来吃饭,饭也很简单,馒头,一个炒菜一个咸菜。黄大妈不让量房事实上还有一个原因,因为想要三套房,但是她自己也觉得按照现在的情况是不可能的,因为她们家房产证上的面积只有130平方米,但是当时每家都有一个1米宽的胡同,加上胡同的面积,应该有160平方米,但是这样还不够-个两居室。如果拖到最后,拆迁办可能会退让,价钱可能还会提高。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剩下最后几户的话很有可能会强制拆迁,国家强制的话肯定就得走了。所以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只能拖着。有一天我们聊天的时候,屋里飞进来两只小燕,黄大妈很快注意到了,说今年小燕又飞回来,但是我们都要走了,还飞回来干啥。两只小燕好像想要在电表上搭窝,但是大妈觉得电表上不结实,说要在门口的梁上钉一块板给小燕搭窝。
“只能拖着”显然是一种无奈之举,是在目前不确定、但最终肯定得走的情况下,对目前步骤的不予配合。“拖”是一种用身体和身体之延伸的家宅的不动触,来表达想要维持原状和抵御变迁的生存心态。拆迁之初,很多村民都对这种行为寄予了比较大的期望,希望用“拖”将他们原本的生活环境维持得更长一些。
5月上旬,周大爷跟笔者讲起在报纸上看到的与北坞村同时进行的大望京试点,大望京已经完成大概3/4的改造,而且有两种可选方案,一种是现金补偿,另一种是现房,现金补偿是按照市场价14000元左右来补偿。北坞村的情况不仅只有一种方案,而且如果仔细算起来的话,实际上一平方米作价7000多元,所以大部分的村民对于这一点也是很不满意的,因为有了大望京的先例,大家的心理就更不平衡了。所以关于北京市对待两个试点的态度,给两个试点的拨款,拨款的去向等,出现了各种猜测,但是大家的态度却不大一样。周大爷认为经不住三问的事情不要随便说,但是黄大妈非常肯定地认为,这笔钱一定是在层层搜刮之下越来越少,最后到了农民手中的就只剩那么一点了。周大爷认为这其实是跟四季青镇的历史有一定关系的,例如,四季青镇实行一级核算,在以往与开发商的合作当中由于没有经验被开发商拿走了大部分的利润,镇政府也没有钱,等等。
在这个阶段,由于大望京试点的政策,两家人都注意到了每平方米14000元的补偿价,心理期望还是比较高的,对于每平方米3000元的补偿价也都不甚满意,但是两者对于价位原因的推断却是完全不同的。由于笔者对这次腾退改造的调查有缺失环节,所以不能妄断哪一种推断是正确的。腾退咨询开始的时候,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周大爷和黄大妈都没有去现场咨询。
黄大妈两年前翻修房子的时候借了28万元,所以她觉得补助首先要能够让他们还账,而且还要能解决以后的生活问题。家里没有劳动力,她听说像他们家这样的算是困难户,可以填一张申请表,别人让她去填,但是她并没有去,所以并不清楚申请表上的具体内容。听说现在每平方米只给1000元,她是肯定不愿意搬的,此前说3000元都不搬,现在1000元哪还有人搬。公布的政策中说,从6月1日到7月15日搬走的人要奖励15万元钱,但是她觉得这15万元并不是平白无故冒出来的,而是从之前定好的价钱里面扣出来的,之前报纸上说的是每平方米3000元,现在如果要是奖励15万元的话,估计每平方米就没有3000元了,所以这可能只是他们采取的一种分化和笼络政策,所以也并没有响应这个提议。黄大妈仍然觉得北坞村要拆迁还是难,最少得过了当年。她们如果要出去周转的话,可能还得租一个两居室,因为还有女儿和外孙女,如果要是楼盖好了再搬的话,不用怎么装修也能搬进去。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