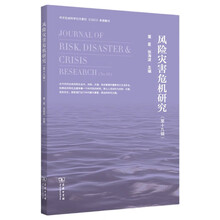并将其描述为一种开明的经验主义。不幸的是,瓦姆斯利自己对这一‘替代方案’的讨论成为了公共行政研究中进一步的异常的例证。对他的许多观点的简短回顾将指出这些困难——特别是由于它们影响了弗雷德里克森对事实和价值的关注。我们将会看到,所谓新社会科学并没有实现事实与价值的和解,反而造成了这些概念糟糕的混淆。”也就是说,所谓“新社会科学”在如何理解事实与价值这一社会科学的传统难题上仍然是模棱两可的,因而也不见得有多少新意。
登哈特认为:“在各个方面,不论新公共行政学还是新社会科学都没有表现出对传统途径特别是逻辑实证主义的大拒绝。举例来说,认为新公共行政学以一种现象学途径为特征,因而拒绝了实证主义的科学观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把新社会科学看作对实证主义传统的实质性背离;它最多代表了对实证主义泛滥的一种谨慎的回应。”要拒绝实证主义,首先必须拒绝实证主义的认识论基础,即事实与价值的二分。在这一点上,登哈特指出,事实与价值的问题实际上是实践与理论的问题,由于实践者需要事实,理论家则呼唤价值,所以理论与实践的脱节就造成了事实与价值的分离。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新公共行政学与新社会科学存在着共同的局限,它们都有意识地与实践保持距离,自然不能解决实践和理论的脱节,也无法替代注重实践——尽管只是一种操作性意义上的实践——的传统,尤其是实证主义研究取向。
尽管如此,新公共行政学与新社会科学的努力仍然是值得肯定的,“公共行政的研究者仍然有很多可以从这些外在于实证科学框架的理论家那里学习的地方”。在登哈特看来,新公共行政学与新社会科学之所以没能达到连接理论与实践、事实与价值的目的,是因为它们没有重视现象学的“praxis”观念。“除非我们真的能够迈向praxis,在社会政治发展的方向上接合反思与行动,否则我们就将受困于旧的二元论。尽管它们也容许某种进步,却将持续性地限制我们的潜能。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