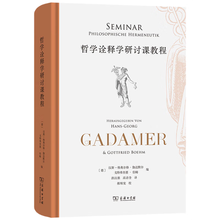个人权能范围就是个人自由的范围,这种自由是任何人都无法加以剥夺的,舍此,则非个人意愿所能主宰,则应听之、任之:“是什么使那么多人迷惘不堪、混乱不堪的呢?是暴君和他的卫兵吗?不,当然不是。本性自由的东西出了它自己以外是不会为任何其他东西所干扰和妨碍的。干扰他的只能是他自己的认识和看法。因为,如果暴君威胁他说,‘我要用镣铐把你的腿锁起来。’珍惜自己双腿的人会说,‘不,饶了我吧。’而珍惜自己意愿的人会说,‘如果你觉得这样对你更有利,那么就锁起来吧。”’②
在儒家的制怒思想之中,义理之怒与血气之怒是严格得到区别的,制怒仅限于血气之怒,义理之怒不可无乃是儒家的共识,但斯多亚派则全盘否定了“怒”本身,对于所谓的义理之怒(义愤),塞涅卡曾花了大量篇幅予以贬斥。常人认为愤怒可以带来勇气,义愤填膺,才能行动果敢,没有义愤,人们面临强敌或凶徒,就会畏手畏脚,而丧失行动的能力。塞涅卡则坚持认为理性无需激情的辅助,“美德不需要邪恶来帮衬;美德本身自我完满。每当需要奋勇斗志的时候,这个斗志不是在愤怒中爆发,而是要审时度势地投入到作战中,就如石弩射出了飞石,飞石的射程要由弓弩手掌控。”③况且,以愤怒对治罪恶,实在是以恶制恶、以暴易暴:“美德不会被允许它自己在遏制邪恶的同时,反而模仿邪恶。在它看来,愤怒本身是要接受惩治的。不端行为引发了愤怒,但愤怒一点儿也不比那不端行为更好,而是常常比它更糟。”④更何况,愤怒根本帮助不了理性,因为理性“只有在远离激情时才具有力量”。一旦诉诸激情(愤怒),激情就会喧宾夺主,因为愤怒一旦形成,它就会胜过试图控制它的力量,把理性席卷而走。理性一旦沾上激情,它就“可能已经丢失了自身”,“理性永远不会求助于那些盲目而不受拘束的冲动,它本身不能驾驭那样的冲动。”①在塞涅卡看来,愤怒在根本上就无法带来勇气,而不过是“给那也许会懒散或者懦弱的人一点儿刺激而已”,“没有谁会由于愤怒而勇敢,除非他缺少了愤怒压根儿就不能勇敢起来。愤怒从来就不是勇气的救助,而是代替了勇气。”②针对适度愤怒可以激励心智等说法,塞涅卡斩钉截铁地说,所谓“适度的激情”,不过是“适度的邪恶”而已。
塞涅卡甚至让人可以设想这样一种情形,一个好人看到他的父亲被杀死、他的母亲被侮辱,他应不应发怒呢?“不,他不应当发作愤怒;他应当惩罚和保护。难道儿子的孝心没有愤怒就不足以投身行动吗?”“好人要做好它的分内,但却不忧不惧;他要做一个好人值得做的事,而不做不应当做的事。‘我的父亲就要被杀死了——我要保护他;他已经被谋害了——我要复仇;这样做不是出于我的痛苦,而是因为我应当。”’③因此,即便在“惹起众怒”的情形下,在“天怒神怨”的处境中,理性之人亦不应有丝毫之愤怒。所谓的义愤,不过是“心智脆弱的表现”。“真正得体而有尊严的做法”,不是非理性地喧闹,而是想办法努力保护亲人与邻居,这是出自义务的召唤,是坚强的意志、冷静的判断与远见的体现。
因此,对罪恶的惩戒应当与愤怒划清界限。惩戒是基于理性,而不是基于愤怒。好的法官在谴责罪恶的行为之时,他是心平气和的,而不应有丝毫的愤怒。毕竟,基于憎恨、基于愤怒去惩戒,对受惩戒者来说很难做到公正,对惩戒人来说,他本身即陷入需要惩戒的激情之中,因而亦即陷入邪恶之中:“任何负有权衡、裁量此等事务责任的人,在掌握了这个需要十分审慎的事物——生杀予夺的权力——时,都必须远离激情的干扰。这是一柄剑,愤怒是一个邪恶的受托人。”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