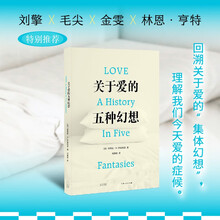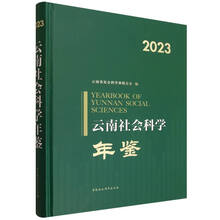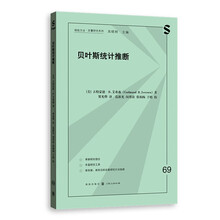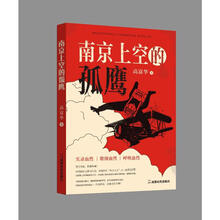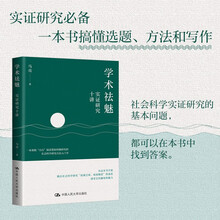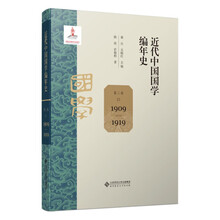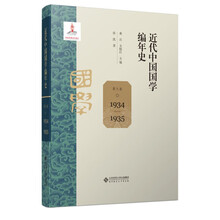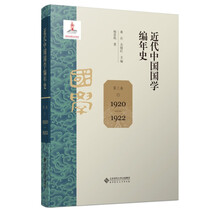二 《诗经》在中国文章体裁方面取得的主要成就
对文章“体裁”这一概念的界定,古今中外亦有极大差异。《现代汉语词典》对这一概念界定为:“文学作品的表现形式。可以用各种标准来分类。”纵观我国文章体裁演变史,有一个从原初的“技法通用”“文体互蕴”到“文体剖判”,逐渐细分的发展脉络。打一个形象的比喻,即原初的文章“始祖鸟”,繁衍出五彩缤纷的众多新鸟类。以《诗》《书》《礼》《易》《春秋》及“三传”为界,我们会发现出于这些著作范围之外的文体很少;而从这些经典向后看,细分文体则呈蓬勃衍生之势。到汉代的刘熙,已在其著作《释名》中将文章分为“书契”和“典艺”两大类,包含细分文体约40种,但主要偏重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实用文体。到晋代,陆机在《文赋》中,从文章形式学的视角已把文体从实用的视角分为10种;萧统编纂《文选》,列出的文体达36种之多,刘勰继承了这种方法,推而广之,在《文心雕龙》中涉及的细分的标准化文体达70种。与他们同时代的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已明确指出了这些细分文体与《诗经》的源流关系,堪称是一篇中国古代文章学杰作。最早提出《诗经》对上古中国文章学有巨大贡献者,当属刘勰,他在《文心雕龙·风骨》中明确提出:“《诗》总六义,风冠其首,斯乃化感之本源,志气之符契也。
是以怊怅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若风骨乏采,则鸷集翰林;采乏风骨,则雉窜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很明显,在刘勰的意识里,《诗经》即是中国古代“文章之鸣凤”。但《诗经》中的诸多文章学成就,刘勰仍未能彻底阐明。明初吴讷著《文章辨体》堪称中国古代文章学又一个里程碑,然于《诗经》发现发明甚少。民国以来,“疑古”风行,诡言眩目,浮论迭出。《诗经》成为任人打扮的“村姑”,许多经典诗作硬被派为“民歌”,但《诗经》中的文章学资源却仍未被严肃认真地系统发掘。
就《诗经》而言,若以古代西方人或秦汉及以前中国文论诸多“大体裁”区分法,它就仅仅是“诗歌”而已。但本文认为,作为元典,《诗经》时代存留至今的文章,尚处于“文体互蕴”的发轫与孕长期。一方面作为“元文体”,《诗经》中所有的作品只是“诗”这一大的分行、韵语语言排列形式;另一方面从“亚文体”的细分化发展脉络看,如果说《易经》是以后预测学与哲学的书写母体,三《礼》是典章制度的书写母体,《书经》是以后政治家政令、演讲和政论的书写范式,那么在《诗经》中实际存在的“亚文体”形态,已为后来的多种新的文学书写样式,特别是赋体、比体、兴体、讽体、雅体、颂体诗歌、韵文及其他相关亚体裁文章,提供了书写范式。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