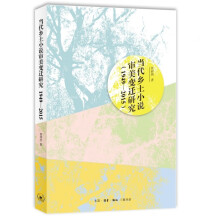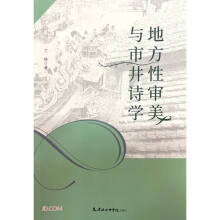分析理性所带来的对自然物的掌握和成功,使得造物主的地位变得虚幻,西方的宗教改革与认知心理模式的确立是同步进行的。于是,人从自然的参与者膨胀为主宰者。传统文化经验系统中对自然“无言馈赠”的限制和虔敬不复存在,宗教的衰落到19世纪中叶已经成为不可扭转的事实,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批判和尼采宣布“上帝已死”,都应看做是重要的历史事件,“人”终于有机会填补上帝死后留下的空缺。但“人”要顶替“上帝”的地位,尚缺乏许多东西,必须在笛卡尔的“我思”理性主体身上注入无所不能的“强力”,方能顶替“无所不能”的上帝。于是尼采呼吁“超人”的到来,其他现代主义者则开掘“人”内在的非理性力量。这样,笛卡尔和康德时代的“认知理性”主体便让位于非理性的主体。<br> 现代文化作为分析理性为主导的文化,科学技术的话语霸权无所不在,它所从事的工作主要是通过分析、解剖、数字计算等,来为整个世界进行符号编码。因此,它与传统文化经验系统的身体劳作与物之物性之间的“交互转让”的有机原则不同,它是先肢解,后编码,它必须首先褫夺任何物的神圣性,包括人体的神圣性,才能完成肢解和编码。数学、天文学、生物学、地质学、化学、物理学、医学等,都在进行着这种编码活动,以便所有自然世界的物都能在实验室被操控、被组合、被复制,并最终转化为资本主义工业制造的批量生产和“流水线复制”。对这种符号编码的最切近的体会,就是去西医医院看病。在那里,你将经历一系列由医疗器械进行的编码程序,体验身体被肢解的恐惧。西医的话语不构成人,它构成疾病。在19世纪还有学者认为,科学技术的编码活动虽然在自然领域取得了凯旋,但人的精神领域却是它的禁区。狄尔泰、柏格森等思想家企图以生命的绵延、创化、体验的不可编码、不可复制性来对抗科学技术符号编码的无限推进和侵略。但就在他们进行对抗的同时,科学技术话语向社会、精神领域的符号编码渗透已经获得成效,并被广泛接受:由生物学衍生出了心理学,财富的计算产生了经济学,传统的语文学在普遍编码活动的刺激下,演变成了现代的语言学。按福柯在《词与物》中的分析,这三个学科主导了人文科学的“范式”作用。当这些学科在功能与规范、冲突与规则、意指与系统之间运作时,它们其实就已经进入了科学技术编码的运作模式之中了。在此情况下,传统的人文学科也不得不接受这种模式的重新整合,就连哲学也不得不从中借助新的资源。从表面上看,哲学领域的“语言转向”是在解决哲学的表达问题,其实是在为源自科学技术的符号编码奠定哲学基础,同时也把哲学纳入了符号编码的过程。<br> 工业制造、资本主义市场交换和科学技术三者结合,把人口、各种资源和财富向城市集中,于是形成了现代社会组织的特有形式:大都市。现代化和都市化是并列在一起的。如果说传统的农耕一手工文化集中体现为一种“乡村经验”的话,那么,现代文化则集中体现为一种“都市经验”。大都市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由财富、生产和人口的人为聚集而成的,它是一个集设计、生产和消费于一体的庞大功能体。都市并非村落的扩大,它把人与自然过程割裂开来,使人彻底遵从符号编码的规则,这个符号编码的规则就是市场的资源配置。乡村社会的“有机系统”被市场符号编码的资源配置肢解得粉碎,人被从乡村有机社会的亲情纽带中撕开,变成单子式的个体,然后再把这些单子式的个体训练成资源配置所形成的劳动分工所需要的单一的“人力资源”;同时,市场符号编码还在另一个层面上,把这些单子式的个体再配置为欲望的载体,配置为“消费者”。都市因此成了开发欲望以便发展消费的发动机。单子式的个体在都市这个欲望发动机中,最终感受到的是孤独、焦虑和自我消亡。波德莱尔是第一个描述这种都市经验的诗人,审美现代性和现代艺术都与这种都市经验相关。<br>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