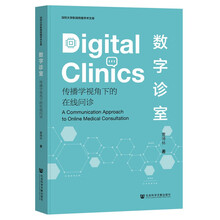第三节 文化的逻辑结构
一到底什么才是“自己文化的发现”
最近B.M.梅茹耶夫(B.M.Mc)Kye的这样一段论述具有代表性:
众所周知,人们曾经长期处于被魔鬼、精灵和神灵等彼岸力量所统治的意识形态下。我们将此称作神话和宗教意识。这种被我们今天视为文化形态的神话与宗教,对于那些对其深信不疑的人来说却不是文化(指人为的),而是来自上面的神圣而不可触及的领域的启示,而现实世界是无法对其进行解释的。在神话与宗教里一切都是由上面的意志所造就的,而人则注定是他们听话的执行者。任何对神灵意志的违背都会招致无法逃避的报复。在这种情况下人的自由独立便会使一切化为乌有,而这个空白的领域便是我们后来所指的文化的领域。
在B.M.梅茹耶夫看来,文化的发现应该被理解为一个完完全全由人自己所创造的存在的领域(或是形式)的发现,这种存在既不是以神的法则为前提,也不是以自然的必然性为前提,而是以从前二者独立出来为前提。文化是按照人的自由法则(当然,如果这种自由是有法则的)而存在的,区别于另一种(自然或是超然的)法则。因此,文化的理解离不开人的主体性。然而,是什么样的具体特征使人能够成为一个主体呢?近代哲学对这个问题只有一种回答:因为人有理性。人是理性的存在,也因此而区别于动物。有了理性才没有让人成为上帝和自然手中的傀儡,而是成为一种独立的存在。理性不仅开创了文化,而且正是文化的最高表现。文化——就是经过理性所加工,并按照理性规律而存在的一切事物。在文化与理性之间画上等号,这意味着是理性(而不是上帝或是自然)为自由建立法规。康德认为,有勇气使用自己的理性,用理性来衡量一切,才是一个有文化教养的人所具备的重要品性,文化不是来源于自然,不是因自然的规定性而存在,而是因为人的自由。作为自由的存在,人会去完成他们自己为自己定下的目标。在目标明确的行为过程中,人便建立了文化。
但西方现代哲学中众多关于理性的讨论充满了危机。概括地说,这个危机的本质就是被理解为人的理性自由的文化却完全不符合人在生活中的实际存在,也就是远离生活。按照B.M.梅茹耶夫的话来说,自由与理性无法同存:自由是个人的,理性是普遍的——任何将两者进行调和的企图都会引发自由的减损和消失的危险。“启蒙理性”(古典哲学的万能理性)不仅成为了认识文化多样性的不易克服的障碍(后古典主义哲学试图通过多种科学研究方法突破这个难点),同时也是人在现实生活中,在自己的实在中自我认识的障碍。在人的“生活世界”,即科学与理论意识以前的世界里,只需要去寻找存在的谜底,与数字、逻辑概念和范畴的合理化世界,即理性的世界都没有任何共同点。在科技合理化与普遍核算和计算生活的数字化的社会里,理性不再是人的自由的同义词,而是新的驾驭人的力量——比前者更加强大。
当理性变成形式合理性,并不再保障自由的时候,自由何以可能?这就促使文化哲学去寻找和构思新的不同于古典范例的文化模式,去重新理解理性的本质,并把理性解释为“交往理性”(哈贝马斯)之后,即要在哲学解释学内寻找关于人的主体性的新观点(伽达默尔)。而在存在主义那里人不再是理性的,他是在畏惧与沉沦之间摇摆,而注定要经历完结的存在,是这种经历滋养了艺术文化。理性与自由的悖论有时候会形成一种印象,那就是自由不再是西方哲学家所关心的问题了——他们更关心的是权利的不同表现形式的问题。权利不会消失,那么让权利在世界生存下去的最好方式就是让权利成为更加可以预知和可控制的,更加合理的,而且看重的即使不是人的自由,也应该是人的基本权益。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