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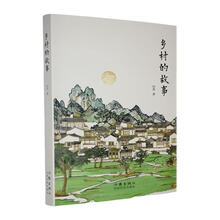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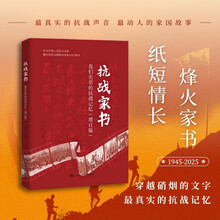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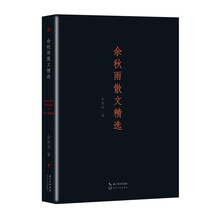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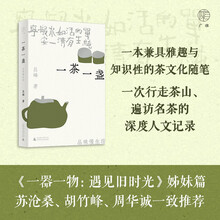
《心中的黄叶》紧紧围绕着半辈子的人生,用艺术的手法,独具的视角,移民+本土的特色,苍凉+华美的笔法,娓娓道来,记录的历史,思考了历史。倾述了人生的价值,和对真善美的执着追求。
西窗烛
“富贵包子!富贵包子!”清晨,阳光熹微,在闹市边缘熙熙攘攘的上班人群中,一个不大的手推车上面搁着一摞热气腾腾的竹篾大蒸笼。一身雪白的围裙、护袖、厨师帽,收拾得清爽利落,一尘不染,甚至连刘海也细心地掖到了帽子里的小贩,一刻不停地招呼着过往的人们。如果不是那清脆的吆喝声,很难一下就断定她的实际性别。
不少人在手推车边驻足了一下,顺手递过一两个硬币,随便聊了几句,接过装着包子的白色纸袋,又匆匆而去。蒸笼上的雾气,随着包子的出售而渐渐淡薄、飘逸。小贩脸上的笑容,也渐渐洋溢、荡漾。在最后几个卖出之后,她会长长地舒一口气,麻利地收拾摊档,将钱袋细心地掖进衣袋,然后轻轻地摘去头上雪白的食品卫生帽。呀!一头乌黑的秀发,即刻在她那白皙的手臂下,瀑布般地泻了下来,在渐渐明朗的晨光中,熠熠生辉;在微微拂动的晨风中,悠悠飘逸。每当这个时候,过往的行人,就会像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似的,忽然发现,这真是一个眉清目秀的姑娘。特别是她那收拾蒸笼时不由自主泛起的甜蜜的微笑,足以使得每一个行人伫足欣赏,留连忘返。
姑娘习惯地用手理了理几缕垂下来的刘海,拎起手推车边挂着的一个老式的军用水壶,一仰脖子,大口大口地喝着水,她确实感到了疲劳,从凌晨开始蒸包子,到全部卖完,这一连四个多小时,没有停歇过。让她欣慰的是,自己亲手制作的包子,几乎每天都能够卖完,周围来往的行人,特别是这些打工的工人们,大都认可了她的包子。每天上门的几乎都是一些老主顾,她也就更加精心地忙活了,特别是注意质量和卫生。
姑娘伸了伸腰,随手取出随身带着的小毛巾,擦了擦脸上的汗水。她的这个动作,很容易让人们识别出她不是来自本土的。今天,在这个城市里,那些本土原住的居民,早就不再使用这类的小毛巾了,那些时常漫天飞舞的纸巾,就是这种不愿使用的结果。
她用手抚摩着光洁如镜的锅盖,洁白似雪的蒸笼布,这是一种爱抚,也是一种自信,这种自信,来自于自幼母亲的教诲,来自于自幼劳动的磨砺。姑娘没有养成的本土习气,或者说本土习惯,她一直保持着自己二十来年受到过的教养和教育。可能这种积淀的素养,就是很多人爱吃她制作早点的原因吧。
一路悠悠,那是有了收获的劳动后的快乐。姑娘不紧不慢地拉着这部小小的手推车,心里在盘算:也许一年以后,就可以开一间属于自己的餐厅了。这让她感觉到了倍增的信心,倍增的勇气,和以前没有的倍增的快乐。她庆幸自己走自己的路,没有错,当年的下岗,那样哀痛的日子,逼上梁山,无路可寻的时候,顺着人流南下,犹豫地推起了这部小小的手推车,点燃起了蒸笼下的炉火,将只求一个简单的生活出路,和着熊熊的炉火,随着冉冉的蒸气,飘荡,飘荡。两年的孤独与艰辛,付出的汗水,让她有了收获,也有了希望。
难得的收获以后的悠闲,难得缓缓地走过闹市,姑娘抬头,欣赏着街景。这以繁华著称的都市,毕竟和家乡的城镇有着截然的不同。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穿梭不停的各色汽车,五光十色的广告屏幕,时尚整洁的过往行人,就连那些和自己一样的沿街小贩,也都展现出与众不同的气质特点。姑娘拢了拢头发,生怕自己的形象影响了市容市貌。她有自己的奋斗目标,不相信那些老板和白领们,都是与生俱来的成功者。
姑娘喜欢在卖完包子以后,一边漫步,一边憧憬,这在家乡可是从来也没有体验过,甚至从来也没有想象过的生活经历。也难怪,家乡的城镇里,什么时候见到过如此繁茂的景致?她记起家乡的那可以数得过来,可以用脚走得过来的几条窄窄的街道,百十个商店,零零散散地散落在方圆几平方公里的市区里,这,在当时,在当地,还算是数得着的城市闹区。那时,上夜班,上白班,交替着的她,每当走过那一片商业区的时候,看着那些小贩们在不停地吆喝着贩卖,还会油然而生一种自豪感——她,文竹,一个有着正式职业的城区居民;她,文竹,就是生活在这片当地最热闹城区的居民。那时,清晨,上白班的时候,她会在一边的摊档上买早点——包子,而且会百般挑剔,什么味道呀,什么卫生呀,什么发酵粉呀,什么面粉精细呀,等,唠叨着掏出几毛、一块的票子,扔给人家,看着他们小心地收拾起来,又赔笑着:
“您,走好!”
那时候,她可做梦也不会想到,这竟然也会是自己的出路。一丝微笑不由自主地爬上姑娘的嘴角,想着这两年的拼搏,她挣下的,可是比当初在家乡的工厂里多了许多呀。这还得感谢厂子里的那帮蛀虫们!每当想到这里,姑娘就想啐一口唾沫,但是,四顾了周围,她,又会忍了下去,不是因为怕罚款,她已经将自己当成这个城市的一分子了,这里的一切,这里的所有,她已经认为和自己密切相连,荣辱与共。这口唾沫,宁愿咽回自己的喉咙里,也决不能糟蹋了干净的街面。
那口唾沫,幽幽地顺着喉管,滑进肚里,心里的火,却因为回忆慢慢地烧着。“那帮蛀虫!”唾沫变成了恨恨的字词,吐了出来。她想到了熟悉的工友,想到了熟悉的车床,也想到了那扇冲着自己关上的厂门。
阳光热烈地舔舐着街道,虽然时仅八点多,在北方,这样的春晨,兴许还会刮着略显寒意的微风呢!“拂面不寒杨柳风”,那正是出游、踏青的绝好时光呀!可那扇冲着自己关上的厂门,却毫不理会明媚的春光,那春风染绿了的大地;毫不理会一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埋头苦干,而惟独不善言语,不善交际,更不善打理领导关系的青春花季的自己。关上了那扇大门,就那样绝情地关上了,将在里面生活、工作了近三年的人儿,堵在了门外。
“厂子亏损,必须精简。”厂长硬邦邦、冷冰冰的话,“你还年轻,还有前途,努力一下,会好的。那几个有年纪的老工人就不同了,是吧?”书记蜜里带苦,笑里藏刀的话。她知道无望了,据说,那几个常常在上班时间去买菜的厂部夫人们,不仅没有下岗,而且还涨了工资
当然,对于那几个厂部夫人,她无可厚非,因为,她们毕竟是上了年纪的老工人。但是,据说厂部的有些人,在这次精简下岗中,大发了一笔。如果,她,文竹,当初要是灵活一点,走一走门路,上贡“研究、研究”(烟酒),她的人生道路可能将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文竹那积压在心中的忧愁,甚至仇恨,就是因为这样,而久久地难以排泄。
一阵微风拂过,手推车上的一包雪白精巧的纸袋漂浮起来,文竹急忙伸手盖住。这些食品纸袋,是她亲自去厂家订做的。她不喜欢那些廉价的塑料袋子,因为知识和经验告诉她,那些塑料袋并不是什么好东西。曾经在农田里看到过那些塑料袋子对农田的污染,让她吃惊。毁了作物,污了田园,损了美观,简直是生存环境里的头号天敌!所以,她的食品袋,经过长期思索、实践,首选了这些卫生、美观、环保而又经济的纸制食品卫生袋。除了包子的沁人心脾,这实质上也是她这个摊点的特色之一。
收拾好食品袋,无意中抬起头来,啊!是他!大庆!文竹又见到了那个小伙子。她高兴极了!在这个远离家乡举目无亲的南方大都市里,大庆,是她遇到的第一个朋友。虽然两人来自不同的省份,甚至语言交流上,还因为各自的家乡方言要磕磕碰碰。但这个小伙子却让她一路来,感到了朋友的欣喜和安慰。特别是那次初识,更使得文竹对他铭记犹新。
说实话,对于摆摊这份小本生意,文竹并不担心自己包子没有销路,从小学就开始做这项家务,到初中就让家访的老师们对她的厨艺怀疑、惊叹,到赞不绝口。而当年的高中同学中,大家又友善地送了她一个“灶王爷”的趣号。她所担心的,就是业界的欺生和人们常说的那些“黑帮”、“保护费”之类的事情。所以,自从开档以来,文竹始终公平交易,决不赚一块昧心钱。她相信,只要做得正,就不怕鬼敲门,她要公公正正地用自己的劳动,推开自己未来的大门。
那是一个微风拂煦的清晨,冬季的南国,和家乡的春天一样,不冷不热,大有“拂面不寒杨柳风”的味道。南下而来的打工者们,行色匆匆,吞下几口早餐,咽下半瓶凉白开,根本顾不得什么风爽叶青,便一头扎进了那些工厂的大门,消失在保安们的吆喝声以及打卡的咔嚓声中了。
一个奇怪的小伙子,匆匆地抓起了两个包子,随手递过来一张十元面钞,接过找回的零钱,没有说什么,转身朝对面的工厂大门奔去。文竹微笑着,看着他那狼狈的背影,心想:这家伙大概快要迟到啦!刚要收拾摊档,没有想到,那家伙又转身折了回来。
“喂!钱找错了!”他把握着零钱的拳头伸了过来。
“少了吗?”文竹有些心虚,因为,她常常会因为算帐绞尽脑汁。
“不——是,多了——本来 元,现在 元!”那家伙翻翻眼睛。
文竹头上开始冒汗了,原来,刚才将十元票子当作了一元毛钞。
她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人找上门来还钱。漂泊的岁月里,见得多了,人们为了金钱,投机取巧、尔虞我诈、欺行霸市;为了一分一厘,朋友翻脸、亲友成仇、兄弟相残、骨肉分离。眼前的这个家伙,竟然会主动退还!对于周围日益富裕的人们来说,数目不大,甚至是微不足道。可这家伙明显是一个和自己一样,为了基本的衣食住行而劳苦奔波的人啊。几块钱,往往是几个小时的收入啊。相信他和自己一样,在一分一厘地,用汗水生存的人。
文竹接过他递过来的几元零钞,没有说什么感激话。因为她在想,按照他的思想和他的行为,很难在今天的社会上发家致富,他永远也只能为别人打工。这样的人本来应该成为和周围那些住在高楼大厦里的人一样,衣冠楚楚,小车当步,不为衣食住行劳心劳力。这才算公平合理。但是,做不到,凭着风雨二十载的经验,她知道,在利益面前不受诱惑,这一点只是文学小说或文人政客的文字诱惑。所以,从内心深处,当她开始对眼前的这个挺帅气的小伙子产生好感和钦佩的时候,也就不希望他成为书本上的那类优秀者,而是实实在在地生活在现实中间。文竹接过零钞以后,有意当着他的面点了点数,然后沉思一下,从中抽出两块递给小伙子。小伙子愣了一下,没有说什么,转身跑回工厂的大门。文竹心里酸楚着,望着那个帅气的背影,也许,以后他就不再是自己的好顾客了。但愿
他以后能够少一些热情,少一些书生气,多一些现实,多一些势利
几天中,文竹一直在渴望着他的到来。来来往往买包子的打工仔、打工妹,不计其数,文竹都没有正眼去看,甚至还有些许的冷淡。至于每天的收入,不像往日那样,精心地去数来点去,更加搞不清楚账目是否对头。
又要收工了,早班的工人都进了厂;夜班的工人,差不多也都走散了。他这时候,应该换了夜班,走过来买宵点了。文竹收拾着摊档,每次专门为他留下的几个包子,依旧静静地躺在蒸笼里。文竹凝视了良久,轻轻地盖上了蒸笼布,叹了一口气。
就在她收拾蒸笼布的时候,两个染着金黄和红色头发的小伙子,游荡着靠了过来。
“喂,小姐,买俩包子。 ”
“对不起!卖完了。”文竹头也不抬地说。
“卖完了?”其中一个动手掀了掀蒸笼:
“不是还有几个吗?”文竹冷着眼睛瞟了对方一下,随手合上蒸笼布:”说完,推起车子。
“留自己吃的。“喂!你搞错了没有!大爷就要吃你的这几个包子!”黄头发的高个子伸手把住了手推车。“不是告诉你了?自家留的!”文竹拐了一下车子。“嘿!又不是不给钱,老子有的是票子,别说吃你几个包子,就是吃你的豆腐,又怎么
样?!”红头发的矮胖子把手向文竹握着车子的手上摸了过来。“你想怎么样!不卖就是不卖,小心我喊警察拉你!”文竹望了一下远处几个游逛的治安员。他们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这边的争吵,依旧说说笑笑地闲聊着。“嘿!警察是我的客户,没有用的——还是给我吃包子吧——”矮胖子的手抓住了文竹。文竹用力甩开那两只肥手,大声叫了起来:
“你们干什么!打劫啊!”矮胖子愣了一下,缩回手,和他的伙伴嬉皮笑脸地站在一边打趣。“干什么的?”远处的治安员游荡过来,轻描淡写地问了一句,眼睛从三个人脸上轻轻地
划了过去。“闹着玩哩——”矮胖子赶紧恭敬地递上烟,打着火。“闹着玩——也不能瞎闹呀!”没等文竹说话,俩治安员便吸着烟转身走了。
文竹愣着眼睛,看着他们晃晃悠悠地踱着方步,走到了街道的另一边。“怎么样?妹子,谁可以管我吃你的豆腐?”矮胖子伸手揽住文竹柔细的腰。“滚开!流氓!”文竹猛地去推他。可是,矮胖子的双手死死地抱住了她的腰肢,很难挣
脱。文竹只好放了手推车,双手猛推矮胖子越靠越近的大嘴巴。柔弱的文竹,怎敌得过一个男人的力气,眼看着那张大嘴巴向着自己的小嘴贴了上来,她,闭上了含着泪光的眼睛
噩梦——一个满是男性汗味的身子,已经靠紧了自己的身体,那两只紧紧地揽住自己的男性的手,揽得更紧了。文竹从来没有这样被一个男人抱住过。虽然,这是一个让她恨透了的流氓,但那种毕竟男人的味道,还是让文竹感到浑身软了,手也已经没有了抵抗的力量。她想大哭大喊,可是,在一片晕眩中,她只感到晕眩。
就在这无奈的噩梦间,那个紧靠近自己的,已经闻到嘴巴烟酒臭味的,男人的身子,猛然间,被人一下子扯开了。
接着就是混乱的打闹声,和自己那辆手推车被撞击的声音。文竹幽幽地,从晕眩中睁开了眼睛。眼前,三个男人翻滚在了一起,浑身都是街上的垃圾:香蕉皮、西红柿皮、苹果皮、鼻涕、痰液等,简直分不清楚他们衣着的颜色。
文竹揉揉眼睛,那是一个熟悉的身影!是他!文竹急忙也冲了上去,生怕他有个什么闪失。“都起来!起来!走!都走!到所里去!”就在文竹冲上去的同时,终于,治安员和巡警那威猛的声音,炸雷般地响了起来
在警所,他们诚惶诚恐地干坐了两个小时,才有几个警察过来录口供和审讯。事情非常明了,文竹被放出,他还要留下,和两个流氓一起进一步审查。文竹刚刚舒了一口气,可一听说他也要留下调查,马上紧张起来。这是怎么回事嘛!他怎么能和两个小流氓一起审查?望着森严的警所和威严的警察,文竹鼓足了勇气,再次对警察们说明了原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