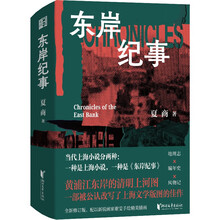这一刻下雪,雪花密集,蜂拥入地,这么声势浩大却又这么寂静无声。 或许是一种象征,这种象征一直伴随着庚伢子降临世界的这一刻,他挣扎得是这么剧烈,呼吸上这个世界的空气之后却又是这么沉默,没有一声啼哭,这叫张圆满大为吃惊,她昂起头虚弱地问:“是死胎吗,九斤大妈?” 这婴孩若是出生时的啼哭特别响亮,也不预示着这世界日后将会吃惊地记住一个姓名;这婴孩出生时如此吓人地沉默不语,也并不显示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庭日后一定会迎来一个又一个惨烈的打击。 九斤大妈为很多妇人接生过,没见过这么沉默的伢子,她的念头是这伢子喉管里有什么异物吧,于是她用左手掌小心地托起婴儿滑腻腻的肚皮,用右手的两只手指轮流敲打着婴儿的背,说:“好像是不情愿托生呢,也不晓得前生是个啥子人物!不过你放心,雷一嫂,不是死胎!” 这一刻是1940年12月18日,窗棂上积着一指厚的雪。火盆上燃着炭,血光满屋,可就是不闻婴儿的啼声。 此时,这个婴儿的父亲、三十三岁的轿工雷明亮,正和二十四岁的同村佃户彭茂林一起,从河码头抬着刚从长沙回来的谭七少爷,一步步前往谭府。当接到六叔公的儿子雷明义的报信,说女人生了一个不会哭的男伢子时,雷明亮马上放下轿杠,对堂弟雷明义说:“你替我一程!” 轿帘掀起了,谭七少爷伸头吼:“姓雷的,敢甩了我?” 雷明亮边跑边喊:“七少爷,我女人生了!让我堂弟替一程!我女人生了!我女人生了!” 谭七少爷指着雷明亮的背影大骂,边骂边钻出轿子:“雷明亮!你小子还是我家佃户不成?你抗上!当年你跟共产党闹,小小年纪当梭镖队长,臭脾气还没改啊?你小心点!” 雷明义哈腰说:“七少爷息怒,我能抬!摔不下您!” 彭茂林绕到轿前,撇撇嘴巴,脸上不好看:“七少爷,府上不远了,一脚就到了,你就快上轿吧!要是不想坐了,你自己走!” 谭七少爷一听这粗声粗气,知道这更是个不好惹的主,村坊间都传言他跟地下赤色分子有瓜葛,于是咽下一口气,再不说话,弯腰钻进了轿子。 回到家的谭七少爷吃饭的时候先是对父亲讲了日本人的动静,又讲了汪精卫的动静,那是他从长沙打探来的,他好几个同学都在省政府做事,消息灵得很。他说日本飞机对重庆轰炸得很凶,老蒋躲来躲去地躲,不过军队倒是收复南宁了,算是好消息,而汪精卫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当“主席 ”了,说到这里谭四滚子就说“汪主席这叫英雄识时务”,随后谭七少爷就说到了佃户雷家的稀罕事,雷一嫂生了个儿子不会出声。 谭四滚子腆着肚子嘿嘿笑,对儿子说:“那是怕时局啊,时局悬喽!” 管家老金也嘿嘿嘿笑,然后咬着七少爷耳朵说:“雷一嫂又见了吗?一直细皮白肉呢,庄稼地里再怎么干活也晒不黑。” 金有德说这话是瞅着七少奶奶没有上桌才放出胆子来的,要是给七少奶奶听见,那可少不得又要撕他耳朵了。七少奶奶肚子大了,这个月都是用人端饭进房伺候的,一天一大碗乌骨鸡汤。 三天后,谭七少爷有了个大胖儿子,这是两个儿子夭折后的第三胎,一过秤八斤八两,谭家上下合不拢嘴,谭七少爷自然更是得意,在吩咐管家上县城求人排了八字以后,为儿子取名喜宝。 谭七少爷抱着喜宝的锦缎襁褓,边踱步边对床上坐月子的老婆皱眉:“ 你看你脸,肿得年糕似的,看人家雷明亮的婆娘,生一个伢,身段模样还那样,生第二个伢,身段模样还那样,管家就那么说的!” 七少奶奶一听这话脸就变色,一会儿就抽搭起来,说:“死不要脸的,在长沙逛窑子,染了花柳病,回村了还盯着人家老婆!” 谭七少爷越看自己老婆越不顺眼,他对金管家说:“我怎么这么背运,老婆抢进门的时候还水灵灵的,不比人家雷明亮的婆娘差,肚子一大,这脸就成红薯了。” 金管家说:“少爷既然这么有心,怎么就不去佃户家看看?”于是三天之后他就陪着谭七少爷踩着雪到了张圆满家,把半篮鸡蛋搁在雷家的破木桌上。 谭七少爷见屋里除了张圆满没其他人,就掀起狐皮袍子一屁股坐上床沿,说:“雷一嫂啊,你男人前几年遭到当兵的一顿打,腰也坏了,肾也坏了,早就没男人样了,废人能给你生出好伢子吗?这伢子一看就晓得生坏了,你看,只有进气没有出气,趁早扔了吧。你这朵鲜花,插在谭家多好!你要生儿子,好呀,我给你生呀,何必死跟着你那半条命的丈夫?” 张圆满大声说:“七少爷,你这番话就不对了!我是雷明亮的女人,这是铁打的,是不是?明亮人好,厚道,我傍着走,踏实!” “你丈夫傍过共产党,当过梭镖队长!” “那是他心善!” 谭七少爷惊讶地皱眉,说:“你敢这么说?” “我老婆说得没错!”雷明亮就是这时候进屋的,原来他听说谭七少爷去了自己家,知道他不安好心,赶紧从渡口赶回来。他一进屋就坐上床沿,捂着腰,喘气,他的陈伤又发了。 谭七少爷赶紧从床边跳开,掸掸狐皮袍子。 张圆满心疼,腾出一只手为坐在床头的丈夫揉腰。这时,一件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她怀里的破布襁褓竟然滑落到地上。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