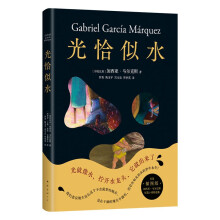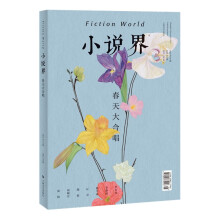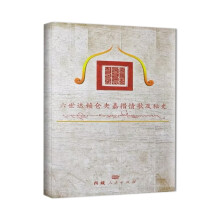我们约会的时间改为两月一次了,主要是曾越,觉得别处更需要他。
可是刚刚才见过半月,曾越打来电话,说他想见我。
我正在写作,虽然没什么灵感,但是每天必须敲出点文字安放自己。
晚上江边茶座见吧,黑,别人看不清你。我说。
现在可以吗?曾越迫不及待。我关了电脑,有些摸不准曾越要说什么?但还是有一种隐隐的激动,为一次可能出乎意料的谈话准备好足够强大的心智。
什么地方?
随便。我诧异他说随便,从来都是他首先找好一个够黑的地方,再打电话给我。
那沙滩长廊见。我脱口而出,带着一种恶作剧。对于习惯在黑暗中坐着的两个人来说,把心灵的秘密晒在阳光下需要勇气。我想看他有没有勇气。
沙滩长廊在江边上,我到达时,已经坐了一些人,打麻将的是多数,尤其是女人。我选择最后一个位子,曾越要到达这个位子,必须穿过那些女人的目光。我内心涌起一种小小的得意,看看曾越是不是像他所说的那样在女人心中有分量。
果然生动。曾越不停地接受那些女人眼光的抚摩,甚至有人站起来和他握手。曾越今天显得特别冷傲。走向我的曾越,一时间满足了我做女人的虚荣。阳光下的曾越算是个风度翩翩的男人。
曾越坐在我对面,却是个害羞的男人,他的眼光不肯与我对接。
在你面前,我像被剥光了。他说。
你是医生,不剥光也知道藏着的器官、血管,小到细胞。我说。其实我也有些难为情,对于这种阳光下的见面,是考验他也是考验我自己。
但是灵魂是遮着的。你看得清我,我却看不清你。
我是牧师啊。
黑天使。曾越说。我们都不自然地笑了一下。曾越把眼光给了只有几只飞鸟的江。
我等着他说下去。曾越打破秩序的约会,也许有出人意料的事情。为了让他有勇气,我要了一瓶干红。
曾越开始喝酒,还是不肯把眼光给我,甚至碰杯的时候,他的眼睛也望着江上某处。江水在阳光下升腾起一层水雾,对岸的高楼像蜃楼似的恍惚。在这种阳光强烈的天气里我总是觉得一切都像假的。我和曾越如此近地坐在一起,却觉得不如黑暗中他离我更近。黑暗中的那个曾越才是真的,他敞开的灵魂里,我看到自己。
曾越不说话,只是喝酒,我耐心地等待,也同样望江。江面上两只鸟上上下下缠着飞,有个男人在拍照,并高声对他的女伴说,情人鸟。
曾越的眼光也追着那两只鸟。我说,有些事并不是我们看见的样子。眼睛和镜头一样只摄下表象。谁说那是情人鸟,也许本来就是陌生的,遇见了,说说话,各自回到原点。
曾越望我一眼,他的眼睛里有许多内容。他说,在阳光下看你,真的很陌生。
其实我和你就像两只陌生的鸟,遇见了说说话。而我正是那种可以在暗处谛听的人。我说。
曾越重复了一句陌生,然后直直地看着我。说,如果你说的是假象呢,或许那就是一对情人鸟。
我重复了他的话,阳光下看你,真的很陌生,好像我们只是在另一个时空见过。
曾越不说话,陌生这个词伤了他,也伤了我自己。灵魂的敞开与倾诉,接纳与谛听,长达十年,我们的心曾在黑暗中互相触摸。
曾越几乎喝了一瓶红酒的三分之二。黄昏已经来临,打牌的男女大都撤退。曾越有些醉了,故作轻松地讲些笑话,但是掩盖不了他的心事。
我问他是否找个黑暗的地方。
没有黑能容下这样的丑恶?一个叫李芬芳的女人,说我对她性骚扰。怎么可能,想起就恶心,你说怎么可能?曾越很激动,声音越来越大。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