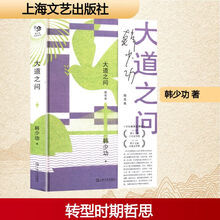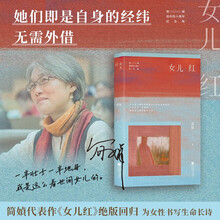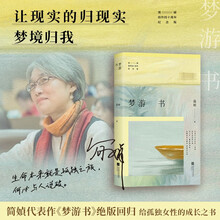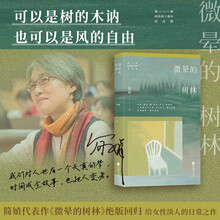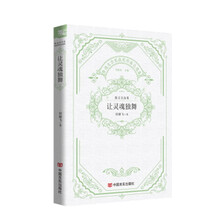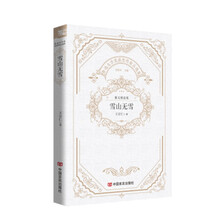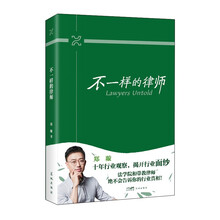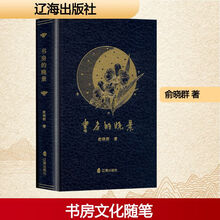在《世说》中,孩子不仅是孩子,更主要的,他们首先是人——具有独立精神的人。其所以如此,与长辈的爱抚和培养是分不开的。《假谲》第十四条:
谢遏年少时,好箸紫罗香囊,垂覆手,太傅患之,而不欲伤其意。乃谲与赌,得即烧之。少年谢玄的这种装饰太女性化了,谢安以谲诈的方法来纠正他的这种不良嗜好,乃是出于对孩子的关怀;而他在为小家伙纠正错误的过程中,又能够充分尊重他的人格,保护他的感情和自尊。谢玄后来成为叱咤风云的一代名将,当然与叔父的这种教育分不开。实际上,在魏晋时期,“人的自觉”意识表现在孩子们的身上,也就是人格的独立和个性的突出。《世说》中的男孩,作为土族子弟,他们生活在自由而富于艺术情调的时代,因而得以保持其精神的独立与性情的本真。他们的自尊自爱,他们的自我个性,获得了充分表现的自由空间。他们是幸运的,也是幸福的!我们看王献之:
王子敬数岁时,尝看诸门生樗蒲,见有胜负,因日:“南风不竞。”门生辈轻其小儿,乃曰:“此郎亦管中窥豹,时见一斑。”子敬嗔目日:“远惭荀奉倩,近愧刘真长。”遂拂衣而去。(《方正》第五十九条)他对“门生”称自己为“郎”十分不满,所以将自己心目中的两个名士偶像抬出来,借以显示其不凡的心志。这样的男孩常常有丝毫也不逊色于成年人的雅量,而在日常生活中显示出穆然清恬的气度:庾太尉风仪伟长,不轻举止,时人皆以为假。亮有大儿数岁,雅重之质,便自如此,人知是天性。温太真尝隐幔怛之,此儿神色恬然,乃徐跪日:“君侯何以为此?”论者谓不减亮。苏峻时遇害。或云:“见阿恭,知元规非假。”(《雅量》第十七条)父亲的美好风仪因儿子的气度得以证明,俗称“有其父必有其子”,又云“龙生龙,凤生凤”,在晋人看来,这一命题的逆向命题也是可以成立的。这种审视方式是非常有趣的。
世界上有孩子,自然就会有描写孩子的文学。但男孩的形象跃动于《世说》的“大人天地”里,却有其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只有对这种背景进行全面而深入的考察,才能理解《世说》所塑造的儿童群像在文化方面的特殊意义。
首先,魏晋世族对子弟培养的重视,造就了《世说》的男孩群像。《言语》第九十二条:“谢太傅问诸子侄:‘子弟亦何预人事,而正欲使其佳?’诸人莫有言者,车骑答日:‘譬如芝兰玉树,欲使其生于阶庭耳。’”“芝兰玉树”决定着家族的未来,所以对子孙后代的培育不可轻忽。“阶庭前长满芝兰玉树,既可自傲,亦可骄人,车骑这句话正反映了世族门第对子弟成长的殷切期望。事实上,世族家族内的每一位长辈也都致力于对子侄辈的培育,言传身教,更利用各种机会和可能,不遗余力地揄扬、提拔同族的后辈,使之尽快脱颖而出。”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