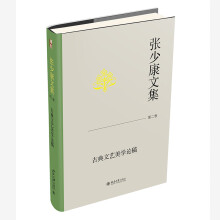小女人的玫瑰梦
文_荆 方
任何一种派系的小吃都必须要有甜有咸才能自成体系。只咸不甜或光辣不酸,都算不上完善的派系。玫瑰切糕就是开封小吃不多的“甜蜜派”中的一分子。在我的印象里,开封的玫瑰切糕都是女孩子在吃。但遗憾的是,少女时代的我是个假小子,从不吃甜的,就爱和弟弟一起站在炭火前龇牙咧嘴地吃烤羊肉串。长大后反而爱上这口了,并且懂了爱吃玫瑰切糕的女人。
卖玫瑰切糕的小车既不像卖泡馍的车一样汤水横流,也不像卖羊杂的车一样腥膻味浓,它一般都被擦得纤尘不染。雪白的糯米切糕平铺在一个锃亮的不锈钢圆盘里,切糕上面用红枣、果脯、果仁摆出一个漂亮的图案。切糕旁边是几排描花的青花小瓷罐,大约有十几个,每个罐里都盛着花花绿绿、令人赏心悦目的配料。
卖切糕的师傅一般是男人。他头戴白色小帽,袖子高高卷到胳膊肘上,打扮得干净利索,神态一丝不苟,全神投入。一个干净严谨的男人本身就会引起女人的好感,何况他还侍弄着这样一个让人喜爱的、美丽的事业,这种细腻、体贴一下就会打动女人的芳心。
再说切糕。开封地处中原,小吃多以筋道、瓷实见长,但这玫瑰切糕却蒸得柔弱无骨、入口即化。卖糕的师傅用小铁铲挖一块抹在盘底,那白莹莹的糯米软软地摊在盘底,像一个娇羞的新娘。挖好糕,师傅端起装有玫瑰汁的壶,把绯红色的玫瑰汁细细地浇上一圈,然后,他以天女散花般的手法把鲜红的玫瑰花瓣、碧绿的葡萄干、焦黄的花生碎、白胖的杏仁等众多配料,一层层地甩在切糕上。
等他终于撒好所有配料,你已经完全目眩神迷。而这时的切糕,俨然有了“三千宠爱在一身”的隆重。你接过玫瑰切糕,慢慢地挖一勺放进嘴里,玫瑰汁浓郁的甜香伴随着糯米软烂的口感,顿时弥漫了口腔。这里没有辛辣和刺激,也没有对抗和征服,有的只是甜蜜中的安适,软糯中的隽永,就像宫殿里的人生,优雅、精致。偶尔一颗杏仁撞到牙齿上,别样的口感和香味更撞起一小波让你回味的涟漪。
玫瑰切糕里的玫瑰汁很重要,它是用玫瑰花瓣加冰糖熬煮成的,清甜香醇。所以吃切糕的顾客时常会要求“添点汁儿”,而师傅也很乐意给你“添点汁儿”。添玫瑰汁不像卖羊肉汤的添汤一样粗率豪放,添汁时,卖糕师傅一边用小壶往你盘里添,一边还会体贴地问你添多少,够不够甜。玫瑰切糕添的不仅是汤汁,更是一份重视和关注。
若干年前,我有一个非常爱吃玫瑰切糕的发小,每次吃到一半,她都像个小公主一样娇滴滴地叫:“添点汁儿呗!”话音未落,卖糕老头就乐滋滋地举着装满玫瑰汁的小壶跑过来,嘴里还不停地念叨着:“给俺妞妞添点汁儿!”当时,我正在满头大汗地吃着被辣椒油泡红的凉皮,对于卖糕老汉“乐于效劳”的表现和这个女孩子的娇嗔颇不以为然。
多年以后,单枪匹马闯荡江湖,才知道作为一个女人,哪怕是小女孩,都有被人宠爱、被人稀罕的渴望;才知道作为一个女人,最大的夙愿就是“有个男人当我如珍似宝”。能够永远做某个男人的公主、一辈子被他捧在手心里是每个女人的梦想,而玫瑰切糕,就是用她甜俗的美梦,把小女人的平淡人生,装点得矜贵无比。
我是传奇
文_纽 西
自从姚明伤退之后,我就没怎么看过NBA。说实在的,NBA让咱这种伪球迷牵肠挂肚的,除了性感迷人的拉拉队队员,不就是姚明这个自己人吗?无姚明,不围观,散了散了。没想到,华裔球员林书豪横空出世,让大家又亢奋了一把。
哈佛大学毕业、拯救球队于水火、在纽约登基的前板凳球员林书豪怎么看都像“别人家的孩子”,但热情的中国球迷没拿他当外人,建议林书豪弃暗投明,精忠报国。幸福来得突然,林书豪说自己仿佛做了一场梦。的确像是一场梦——“美国梦”,换个很中国的说法,叫“传奇”。
王菲唱过一首情歌也叫“传奇”。那时候,天后还不走音,一曲唱罢,余音绕梁。因为爱情,情人节前夕,澳大利亚帅哥尼克·胡哲和亚裔美女宫原佳苗步入了婚姻殿堂。30岁的“海豹人”尼克·胡哲天生没有四肢,凭着乐观的天性和超凡的坚毅,拿下了两个大学学位,骑马、冲浪、游泳、足球也是样样在行。尼克走遍世界,向人们讲述他的传奇,顺便解决了人生大事,没有“剩”在当下,这段良缘难得地让人羡慕嫉妒没有恨。
偶像的力量是无穷的——总有一种让人羞愧难当的感觉。震撼人心的不单是大洋彼岸的豪哥和尼克,还有小人物书写的传奇。拥有众多女“粉丝”的《读者·原创版》作者苏晟辞职之后,萌生了骑行川藏线的念头。苏晟在QQ上给我留言:“如果这次不去,下次只怕是几年之后了,我不想留下遗憾。”这个体重从未过百、骑行经历为零的哥们儿,就这样一点一点消化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带着伤痛胜利抵达拉萨。张广柱和王钟津这对花甲老人则颠覆了传统的养老方式,4年间携手环游世界,这段浪漫之旅和他们童话般的爱情让无数年轻人艳羡。
看到这期特别报道的时候,我猛然想起那个众所周知的笑话:中国的时尚杂志,就是一群月薪8000元的编辑告诉一群月薪3000元的读者,月收入3万的人怎么花钱。套用这个说法,《读者·原创版》一群基本没有出国经历的编辑,为读者描绘了一堆牛人怎样挑战自我、环游世界——看哪,小人物也能化身传奇!
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环游世界的梦想。我们都羡慕那些在路上的人,渴望有一天能像他们一样背包上路。我们之所以至今停留在原地,或因俗务缠身,或因缺少勇气,但每当看到这样的故事,仍然蠢蠢欲动,想要分享。天气渐暖,是到处去走走的时候了。其实,季节并不重要,年龄也不是问题,只要你渴望上路。说到底,旅行就是一场身体和心灵的修行。
有多远就走多远。
疯狂的面包
文_王莹莹
这里是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黑庄户乡苏家屯的一家精神病托管中心,它隐藏于安静的村庄中。红色的大铁门紧锁着,出入需要登记,因为这里的病人都处于精神疾病康复期,仍然有不同程度的精神障碍、分裂乃至缺损。院内非常整洁,四四方方的天井,阳光暖融融地洒入。基本每天上午,病人们都会在院子里做早操,接受种种康复训练,比如零件组装、食堂帮厨,还要会学习刷牙、洗脸、穿衣等基本生活技能。
上午9点半,多数病人已经回到房间里休息,整个小院安安静静的,但是有一个角落却格外忙碌。伴随着阵阵喧闹声,满满一炉面包新鲜出炉,那来自生活的浓香如同阳光,不偏不倚地温暖了这个偏僻的角落。我们这里有点不一样娜塔莎和伊万早已经到了面包制作间。操作台上摆着几个大簸箕,里面盛着数十个新出炉的面包。
这里一共有5位面包师,他们的另一个身份是精神病患者,但此时此刻,看不出他们有任何异样。从早晨6点钟到现在,大家一共做出69个德国麻花。根据娜塔莎带来的订单,大家先把面包一一装进纸袋,然后把订户信息写在袋子上并仔细核对姓名、电话、住址、面包品种等,最后再封上面包标签——CrazyBake。“Crazy在英语中只有一点点‘精神病’的意思,更多的是疯狂、激情,好的意思居多。”伊万解释道,“这个名字很好,很像我们!”
伊万是瑞士人,说话快而有力,1994年跟随中国丈夫来到北京。十几年来,她的西方式独立与中国式传统渐渐取得一种平衡,同时她也从一名心理医生成为精神疾病志愿者,日子过得坚定而明朗。
娜塔莎是一名德国家庭主妇,有3个孩子。相比伊万,她显得安静而温和。自从开始做“疯狂面包”,她的生活就忙碌了许多,不仅要教患者们做面包,还负责送面包。比如今天是星期五,她要送50多个面包,从早上11点出发,真正回到家里休息,恐怕得到下午4点钟了。
随着物价上涨,“疯狂面包”的售价也从每个15元涨到25元,但相比北京的其他外国面包,这个价位只是中档。春节期间,伊万回瑞士探亲,惊讶地发现中国的面粉、白糖、鸡蛋、食用油居然比瑞士还贵。“怎么可能?”她到现在也不明白。除了物价,她不明白的东西还有很多。比如,8年来她们一直试图找人帮忙送面包,但总是没有人答应,大家都说“我很忙”。所以直到今天,“疯狂面包”基本都由伊万和娜塔莎完成每周两次的送货上门。北京的天气阴晴不定,烈日、狂风、骤雨、沙尘暴……这些都没有影响面包的送达。
怀孕期间,伊万照样挺着大肚子教大伙做面包,生完小孩才两周便用提篮提着宝宝来面包房工作。娜塔莎也一样,怀孕、生育也没有耽误面包房一天的工作。孩子学习爬行时,就在面包房里满地爬。“她们真的很了不起!”护士长杨云说,并且调侃,“她们和我们不一样,身体也不一样。”“怎么不一样?”伊万大声纠正,“身体一模一样,只是想法不一样。”
谁比谁更疯狂
的确,不同的想法决定了不同的人生。
伊万在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心理学专业毕业后,成为一名心理医生。因为长期与精神病患者接触,所以伊万来到北京后也自然而然地走入精神病患者这个圈子,并与他们交上朋友。“刚开始在医院里接触到患者,有时我晚上回到家里会哭,”伊万说,“因为我感觉自己的生活太好了,我有丈夫,有孩子,有住房。可是他们什么都没有……”
娜塔莎的先生也是一名精神疾病工作者,受国际残障组织的邀请,来到北京精神病托管中心教授英语。为了帮助患者恢复劳动能力,他们在托管中心开辟了一个菜园,带领大家一起种菜,但种菜受季节限制很大,如何帮助大家实现有规律的、持续性的劳动?他们想到了做面包。
“刚开始提出这个想法时,患者觉得我们比他们还疯狂。”伊万说,“他们从没做过,也没有兴趣学,更认为没人会买他们的面包。”
“因为他们很多年没干活了,认为自己是病人,是来休息疗养的,怎么可以干活呢?”杨云说,“但我觉得非常好,因为手指运动对他们的大脑恢复非常有帮助。”于是她开始做大量的说服工作。
尽管质疑声不绝于耳,娜塔莎还是向亲朋好友发出邮件,希望获得爱心捐助。50欧元、100欧元……她们共收到近20笔捐款。于是大家把托管中心的一间旧厨房改造成面包操作间,购置了两台大型烤箱,还定做了操作台及基本工具。伊万还找到一位设计师朋友,在一小时内完成了“疯狂面包”的标志设计,“因为他只有一小时是免费的,容不得我们有太多思考”。
随着“疯狂面包房”雏形初现,一些坚决反对的患者也终于同意试一试。你可以设想那时起步的艰难:和面、醒面,学习如何加入黄油、如何刷鸡蛋、如何掌握烘烤时间及温度……即使是能够熟练做馒头的杨云也不得不承认:“做面包比做馒头难几十倍。”
以最简单的德国大麻花为例,四股面如何漂亮地编织成形且不黏滞,如何均匀地刷上蜂蜜、蛋清……刚开始的产品总是失败的,要么烤煳了,要么硬得像石头,但伊万和娜塔莎总是鼓励大家:“还好,还好!”当然有顾客抱怨。每到此时,娜塔莎只好笑着说:“这次免费好了,下次我们送给你更好的。”当然,这样的打击她们没有告诉患者。
为了避免浪费,她们始终保持以销定产的订单方式,同时,出于对品质的考虑,她们把面包的产量定得很低,哪怕一天只做几个。
关于赢利,她们不会考虑太多。因为做“疯狂面包”的目的不是销售,而是通过手指与四肢的运动帮助病人恢复健康。所以在面包制作过程中,除了教授,她们更重要的一个工作是观察病人的情绪,每当碰到病人情绪焦躁,她们会立刻让他停下来休息。
石师傅是一名严重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从“疯狂面包”成立起便一直在面包房工作,当然中间也有数次犯病的时候。有一次杨云发现他怎么也团不好面团,情绪越来越紧张,差点和旁人打起来,于是强迫他停下来。休息治疗一段时间之后,石师傅找到杨云说:“护士长,我还想做面包。”
高兴从里面来
终于,他们喜欢上了做面包。
终于,“疯狂面包”越来越漂亮、香甜。在日复一日的规律劳动中,这些精神病患者也渐渐建立了自我认知,不仅意识到自己患有精神疾病,而且也建立起自己是个面包师的自我认知。“当这两种认知同时存在时,他们便建立了社会责任感。”杨云说,“这个认识是病情恢复非常重要的指标。”
2007年8月,利用“疯狂面包房”的赢利,娜塔莎和伊万在托管中心附近租了一处独幢别墅。托管中心经过专业的衡量,认为几位面包师恢复良好,可以出去生活了。搬家那天,大家一起热热闹闹地去市场买来水盆、水桶、锅具、饭碗……一起去菜场买菜,一起挤在厨房里做饭。“想吃什么就做什么,喜欢什么就买什么。”一位患者快乐地说,“真是太棒了!”
石师傅的弟弟一直在德国生活。因为牵挂哥哥,他总是定期过来探望。最近一次探望,他惊讶地发现哥哥变了许多,不再像以前那样懒散了,暴力倾向也减轻了许多。临走时,他买了一个“疯狂面包”,嗅着哥哥亲自烤制的面包,他开心地告诉杨云:“这是我离开时最欣慰的一次。”
从2004年至今,“疯狂面包”已经“疯狂”传递8年了。8年时间,在巨大的北京城里可以发生多少事情?但是在“疯狂面包”的操作间,娜塔莎和伊万始终以志愿者的身份手把手地教会一个又一个精神病患者做面包,并且开着小货车、踩着自行车风雨无阻地穿行在北京的车水马龙中,把“疯狂面包”一一派送出
去。又或许,这不仅是面包,更是一份浓浓的关爱。
许多人觉得她们疯狂。但什么是疯狂?伊万用力挥了一下手,说:“我们一点也不疯狂,我倒感觉花那么多钱买一辆捷豹的人更疯狂!”而娜塔莎的解释是:“因为我们生活得很好,我是一个家庭主妇,不是很忙,又不喜欢做美容、做头发,那么就帮助大家做面包好了。”
这样的理由简单得令人失望。或许公益真的不需要煽情的理由,不需要背负宏大的使命,或许公益就是量力而行、身体力行、举手之劳。作为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伊万和娜塔莎注意到中国人的房子越来越大,车子越来越高档……可是大家真的高兴了吗?她们时常怀疑。“什么是高兴?发自内心的高兴才是高兴,如果你的生活好了,你应该去帮助别人,让别人也好起来,只有这样你才会高兴。”伊万说着,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胸口,“因为高兴是从里面来的。”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