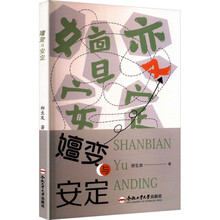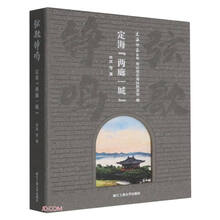我心底永不消失的歌,源于红色圣地西柏坡。
红色圣地系在我的心中,只要闪过,头脑就感到清新,胸怀就感到宽阔,脚步就迈得轻省。西柏坡村中又有我多家亲戚,我只要回到故乡,就要赴圣地“胸怀宽阔”,再往亲戚家里情河奔流。
新中国诞生之后,我喜坐阎九林老叔的炕头。老叔在硝烟弥漫中与我的父亲结拜,我与老叔的亲近就如我的父亲。老叔首先惬意地告诉我说他宴请朱德吃他的佳肴。
那是党中央进驻西柏坡不久,朱德参与乡亲们在村北沟谷中栽植白杨,朱德掘坑之用力,植树之熟练,神情之平朴,言谈之亲切,活似乡亲们中的一个。午时归家,老叔与朱德并行。老叔随意地说:朱老总到我家吃饭?朱德谦和地笑笑,与老叔幽默:“让朱老总吃山珍海味?”老叔与朱德风趣:“朱老总,我给你改善生活。”老叔为朱德摆于饭桌上的是掺菜的玉米面饼子、多菜少米的菜饭,朱德如吃下山珍海味,连吃两个饼子、两碗菜饭。朱德留足钱票粮票,再与老叔亲切:“我改日再来吃你的佳肴。”
老叔又与我自豪地述说毛泽东朝他拜师。
南瓜开始探蔓的时候。下午,云淡风轻。老叔独自在园田里聚精会神地培育南瓜秧苗。晚饭后散步的毛泽东突然站立在他的头前,惊喜得他如同耳闻一声春雷,他忘记向毛泽东问好。旧社会,他祖辈父辈用生命换来的财富多半落人富人手里,住不得温,食不得饱,穿不得暖,又没有避开国民党的监牢。他心里有了朱、毛红军,才意识到他是个人。他已看到朱德、周恩来的平朴,还未目睹毛泽东的平易。“哈哈,西柏坡,大都姓阎王爷的阎,你也和阎王爷是一家吧?”毛泽东主动与老叔搭讪,平易、亲切而又风趣。
老叔惊喜难息,等毛泽东再与他平易、亲切一番之后,他便习惯地挺一挺胸膛,晃一晃膀子,自豪地但却文不对题地启齿:“我阎九林很不简单!”“你阎九林的确很不简单,瞧你培育的瓜秧多么肥壮!”毛泽东笑呵呵地赞扬着老叔,伸手拉一拉老叔,同老叔一起蹲下说道几句家常,要过老叔的小锄,要跟老叔学习培育瓜秧:“老阎啊,我们不能只动口不动手。请您允许我拜您为师,跟您学徒,教会我如何栽培瓜秧好吗?”老叔竟然心血来潮,忘记毛泽东是党的领袖,他崇拜的伟人,他应诺为毛主席做师,应得痛快淋漓:“主席,成!成!”毛泽东只让老叔动口不动手。老叔吩咐毛泽东将一株疯长的瓜蔓拧两遭再压入坑内,毛泽东害怕瓜秧受损,一拧未拧埋进坑里。老叔不禁发火:“不拧它两遭埋下就会长疯不给结瓜!知道不知道?……”老叔很快意识到自己走火,迅疾停顿。毛泽东更加平易、亲切:“说嘛,说嘛!”“我脾气不好。”“没有关系,严师出高徒嘛!……”
午时,嫂子在炕上放妥饭桌、老叔从墙堂里取出一瓶红枣老酒,再从柜底取出一张略小于手掌大的照片,照片微黄,而我一眼看真,我凝神屏息。
“润身,这是毛主席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送我的毛主席的照片。”老叔在炕边坐下,一字一句:“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毛主席在陕北准备东渡黄河,朝我们这里转移,向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们要往白毛女的故乡去了。你把照片收藏起来。你看毛主席多么慈祥,多么亲切!”
我心头一热,回到我的老家。我不知从何时起,父亲欠下债主360吊铜钱,利息三分五厘。勤劳善良的父亲日日披星戴月,忘命汗流浃背,一家人入冬难添一件新棉衣,年节难见一顿白面饺子。父亲将为逃债落井的邻居嫂子救出,父亲又把井看为天堂,无我阻拦,父亲就告别了苦寒。我即将长到锨柄之高,我看到两张地下其产党员散发的传单,不禁挺一挺胸膛,心里刻下朱、毛红军和毛泽东的名字。卢沟桥遭受侵略者践踏不久,我告别父母,披带了《八路》臂章,便跟毛泽东爬过雪山走过草地的队长亲切地喊起小鬼。开始懂得什么是幸福。
我郑重地向父亲般的老叔连敬三杯红枣老酒,愉悦地接过我梦寐以求的毛泽东的照片。翌日早晨,老叔还未起床,我步人西柏坡纪念馆一侧的柏林散步,健步登上顶峰,昂首面向灿烂的朝阳,纵情歌唱乡亲们心上之歌。从此,仿佛是一条红线将我梦寐以求之照片和我纵情歌唱之歌拴连在一起;照片放于笔记本内,歌存于心底,我只要独自看到照片,就要哼唱三句五句。
我万万料想不到,因为言实,我在反右倾运动中遭遇批判;“文革”开始,江青在首都千人大会上对我点名,说我写的颂扬革命情谊的电影《探亲记》修到家了,令我家破人散,还要朝我心上猛击一掌。一天,戴红袖章的男女从牛棚中将我揪出,押我回到寒舍,查抄我的存款。我的幸福观中没有金钱,所得奖金、稿费大部分交了党费。失望到家的戴红袖章的男女还不罢休,搜出我参与编剧的电影《白毛女》获得的金质奖章,和在红色圣地拿到的毛泽东的照片。
“你配!”戴红袖章的男女气势汹汹,众口一词。
已习惯于双目不睁、口舌无声的我,不畏皮肉被触及的灵魂脱壳,双目不睁,口舌无声。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