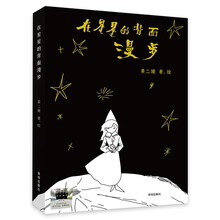他换了一个姿势打量灰土里的父亲,父亲的眼睛和嘴都是一副勉为其难的样子。这大概就是人们说的苦脸了。苦脸家伙,最难对付,也最难改造。
一张愁苦的脸,怎么才能画出笑容来呢?天完全黑了,四海收兵,等着改天再战。
农人每天收工回家,习惯一声不吭坐在后炕上。那是他作为一家之长该坐的地方。顺山大炕上,烂席子上东补一疙瘩布,西纳一疙瘩塑料,只在他常坐的地方铺了一块旧毛毡。几乎每个“海子”小时候都在那块毛毡上拉过屎、撒过尿,白毛毡被他们的娘擦洗得年头多了,陷进去一块,突起来一条,早就变成了世界地形图。那些年,他们的爹一出家门,他们就去抢占那块毡子,谁坐上谁就像王,尽情享受毛毡子软乎乎的好处。爹一回家,他们赶紧腾地儿让坐,躲得爹远远的。
农人似乎什么也没有看见,他回到家,就沉浸在高强度劳动后身心终于和缓的安详中。脸上的皱折因为猛吸烟袋,突然鼓胀了一下,随着一口烟喷吐出去,那些沟沟坎坎又都弯曲下来了。
农人的快乐是没有结果的,就像农人的苦难没有结果一样。
农人平常不大说话。也许是苦寒惯了?天黑以后凑到队部开会,等书记、队长讲完,他顶多接下茬,说个笑话:“大哥念完我念,一步迈到当院,一脚踩塌个猪圈,猪娃子跑下一院。”大伙干干地笑两声,散伙,回家,睡觉。此时,他心里在想什么?农人有一次说了一句苦幽默:“咱们农民没来由,一年到头背死牛。”这话被下乡干部加工加工,变成:“这个老汉没来由,一学毛选就走正路。”农人听了,被逗得嘿嘿直笑,一笑:“你说人家也爱编排个顺口溜溜啊?”二笑:“这话也有些道理哩!”他高兴起来。为感谢干部,把干部领到他家吃了一顿尽了全力但干部仍然苦不堪言的晚饭。一撂下饭碗,干部拔腿跑掉了,农人冲他喊一声:“王领导走呀?慢慢走,黑天打洞的!”他跳下炕送走王领导,仍旧坐回炕角,吸他的烟袋锅。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