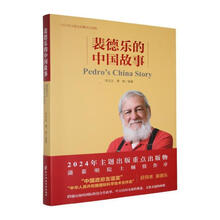域外之际
从“新村”到“鼓童村”
日本的“新村”在中国颇有些名气,至今还常出现在现代文学研究者的文字里。我去日本前,以为它早已消失,和武者小路实笃的逝去一同逝去了。不料在东京友人嘴中,却还能听到它的名字,这才知道“新村”还存在着,不像中国的“人民公社”,已成历史的旧迹了。我对“新村”的一点兴趣,说起来是缘于周作人。l919年五月,周氏得到东京“新村”支部函,邀其访问。七月七日,他由武者小路实笃陪同,在“新村”所在的石河内村住了多日,不久周氏便把《访日本新村记》登在《新潮》杂志上,在国内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连青年毛泽东也被此感染,还亲自到八道湾拜访过周氏。现代中国农村的乌托邦之梦,最初是与“新村”的名字有些瓜葛的。如果有人对苏联的“集体农庄”与日本的“新村”作一个比较,看它们对中国的影响,当会引出许多话题的。
“新村”是一个松散的组织,村庄的工作与生活都处于一种自由、平等的状态,过着“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生活。很有一点卡尔·马克思的幻影。1920年6月,周作人在《晨报》上撰文介绍说:
他们现在的生活,因为物质力的缺乏的缘故,很是简陋,看来或有很像中国古代的隐逸,——虽然这
些详细的生活情形,我们是毫不知道,——但那精神完全是新村的,具体而微,却又极鲜明确定的,互助与独立的生活。——他们相信人如不互相帮助,不能得幸福的生活,决不是可以跳出社会,去过荒岛的生活的。他们又相信只要不与人类的意志——社会进化
的法则相违反,人的个性是应该自由发展的。这种生活的可能,他们想用了自己实行的例来证明他。这件事可以说有了几分的成功,安全的生活的确定,还要略等时间的经过,其余试验的成效多是很好。他们每天工作,现在暂定八小时,但因了自己的特别的原因,多少也自由的。工作是分工的,现在只是农作,但不是如孟子所说的并耕。他们不预备在现今经济制度底下,和资本的组织去角逐,所以不必要的剧烈劳动,在男子也努力免去。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