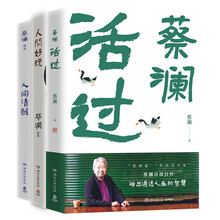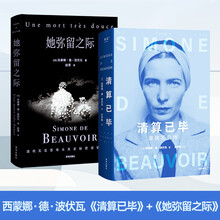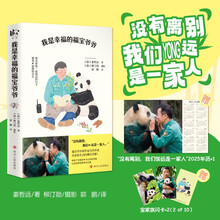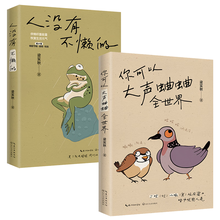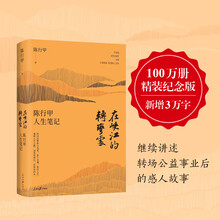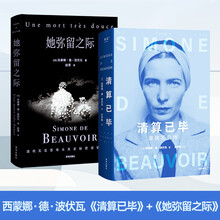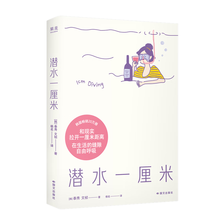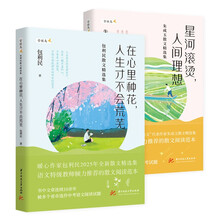石头的生命
我见过皇帝陵前的石人石马,呆滞、僵冷——那是一种静止了的严峻;我见过深山古庙的石刻石碑,沉默、拙重——那是一段凝固了的历史。
于是我想,世上最缺乏活气的,恐怕要数石头了。人们常常形容:“这人冷得像块石头。”“那人呆得像尊石雕!”
可有一天,我忽然相信了:石头也有体温,也会呼吸!
瞧,眼前一尊石刻的舞伎活起来了——她身姿构成优美的s形曲线,肩披一条像空气般透明的纱裙,宛如梦想的羽翼,飘逸的纹饰表现出舞蹈的节奏,使沉重的石头完全失去了重量,变得轻虚空灵了……
这是我在龙门石窟一个并不显眼的角落里,发现的小小奇迹。
位于洛阳之南的龙门石窟,是我国三大艺术宝库之一。它密布于伊水两岸的崖壁间,东西长达一公里。
走进这个古代人物画廊,我简直难以置信,它是石头世界构成的!
我的注意力首先被惊心动魄的“庞然大物”吸引。从开凿于北魏时期的一宾阳洞,到唐代的奉先寺,一尊尊大佛,须仰视才能看见,愈加衬出人的现实地位的渺小。奉先寺的卢舍那大佛,足有六七层楼高。据说这就是武则天的化身。当年,这个崇佛抑道的女皇,匍匐在神像前,她也要求人民如她拜倒在神的脚下一样,匍匐在她面前。于是,她慷慨拿出一笔自己的脂粉钱,捐赠二万贯,用以建造这一描摹佛回天堂的辉煌洞窟。她自己则摇身变成了天堂的主角——卢舍那大佛。
这是石雕艺术的绝妙精品。大佛全身笼罩在沉寂的光晕中。洞悉哲理的思辨神情,难以言说的深意微笑。眉宇间既糅进了一种冷漠的智慧,暗示出几分帝王的威仪;嘴角边又浮现了温雅的柔情,给人以人类之母的慈爱。她似乎是高出于人间又接近人间,令人敬畏又使人感到亲切。整个形象构成了朦胧、神秘、含蓄的美感。武则天正希望达到这样的效果:让自己作为神的化身来永远统治人间。
不过,神,毕竟是供人朝拜的偶像。它缺乏活的生气。纵观这里的大佛,总有一种规范化了的单调感,统一的坐态、统一的螺发、统一的表情。从佛的头顶至双肩、双膝,可以画出三角形的连线,这使我想起三角形的稳定性。它固然增强了佛像的和谐与内向,却也加重了佛像的呆板、沉闷。那种超然于世外,去尽人间烟火味的居高临下姿态,总让人感到:那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就在这时,我一眼瞥见了佛像莲花座下面的小小舞伎。活跃飘动的线条旋律,绕着蓬勃的生气,颤动的柔软,人体那么轻盈,仿佛要离开大地,乘风归去。我忍不住蹲下身子去抚摸,果真是石头!石头也会复活么?
“快看,这个小人儿多活!”猫着腰在另一个角落觅宝的老章又发出欢呼。嗬,是÷个供养人。他生活在现实的人间,嘴角流露出喜欢开玩笑的轻松特征,微微嘬着口,似乎正往外吹气呢。雕刻匠抓住了人物瞬间的神情、动势,使之个性爽然毕现。哦,这种生活小景也进人了佛国圣地?
更有趣的,是某些小神龛里的菩萨也走向了世俗。有一尊小佛,别看它表面上盘腿端坐,右手掌心向外,似乎在屈指讲经,其实,它左手却在偷偷地抚弄足趾玩哩。莫非人世的生活战胜了天国的信仰,它终于耐不住神龛的寂寞,欲步下莲台追赶人间的欢乐……
作为陪衬大佛的各种“小角色”——在飞天、力士到供养人身上,往往活跃着真实的生命。正像一组跳荡的音符,衬托出凝重的主旋律。我感到纳闷,为什么不属“正宗”的小人儿,反而能雕“活”?
画家老高的话启迪了我。“正宗者,是高不可攀的神;陪衬者,是世俗化了的人。”雕刻佛像,必须受到宗教“仪轨”的束缚,一切都被“仪轨”牢牢地限定住了,也就免不了千佛一面。而雕凿小人儿时,刀法可以有个性地发挥,有时寥寥数笔,似乎漫不经心,人物却天然趣成。它不拘一格而自成一格,丰富、多变……
听说大足石刻神的形象已完全人间化。宗教教义让位于现实艺术。更多的世俗小景出现了。有位朋友陪同一对日本夫妇去参观。一个个呼之欲出的民间人物,把参观者困在了魔术环里。那石雕的放牧少年,脸上浮现出天真烂漫的微笑,可爱极了。怡然出神的日本女士,以多情的目光流盼着石人。忽然,女士情不自禁地上前拥抱他,热烈地和这石人亲起嘴来。亲了满满一嘴唇的小粒砂石,还满不在乎地回头朝自己丈夫笑哩,边笑边逗她丈夫:“你还,不如这石雕美呢。”“那你就跟放牧少年年结婚去吧,哈哈……”
这是艺术的魅力!希腊神话中,就有这么一个故事:塞浦路斯王深深地迷恋上自己用象牙雕成的美丽少女。于是,祈求爱神赋予雕像以生命,和少女结成了夫妻。
艺术,给僵冷的石头注入了生命。它无视时间。一千多年了,古代艺匠们创造的生命还在这里呼吸,古老石窟的肺腑因之而搏动起来。尽管那些无名氏,在没留任何名字的雕刻作品中消失了。但祖先的智慧,却在这里凝固了——这是一种终于凝固于空间的旋律。
不过,假若艺匠们的雕刻刀更少地受一点宗教仪轨的束缚,那么,活的艺术形象,岂不将以更多的姿态从岩石间,跳跃而出了吗?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