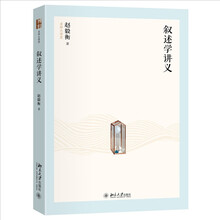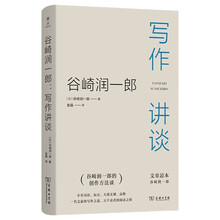从才、学并举,到才、气并重,这一转变基本上是在南渡时期完成的,“学”的问题被淡化、包融在“气”的范畴之内。诗学观念的这一变化,与道学的初步扩张同步,为我们考察诗坛与道学的关系提供了新的例证和突破口。绍兴五年(1135)李纲为邹浩文集作序时说:“士之养气,刚大塞乎天壤,忘利害而外生死,胸中超然,则发为文章,自其胸襟流出,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李纲之所以如此重视“气”,因为它不仅影响士人的行为,还影响到文章的成效;就像邹浩,他坚贞的节操始终如一,“自其少时,处闾里,游庠序,登仕途,其节操风流,已为有识者之所推许。至元符间,职在谏省,适有椒房之事,抗章陈列,危言鲠论,耸动四方,远谪万里。及建中靖国间,召还侍从,又以直道不容于朝,再谪岭表,而气不为之少挫。遇赦得归,作知恩堂以居,奉其母,友其诸弟,教训其子侄,欣然不知老之将至。所养如此,故其文章高明闳远,温厚深醇,追古作者”①。南渡前后,对“气”的推重,有鲜明的时代性,目的是激励士人要临大节而不可夺。如李纲在《跋张嵇仲枢密遗稿二》中说:“士之立名节、死国事,虽志气有所感激,其平时胸次所养,必有大过人者,遇事而发,非偶然也。”②所以,胸中之气象,首先应当是一种人格修养;其次流露在文章之中,则中正平和。以此之故,在李纲看来,历史上的忠臣义士,一致的特征便是“以气作之”,所以看到刚介的梅和胜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每读前史,见古人立名节大略,率以气作之。和胜刚介,自喜胸中之气,常勃勃然,宜其临事不苟,挺挺有古风烈也。”③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