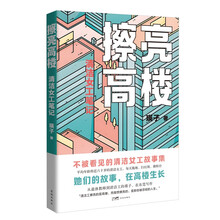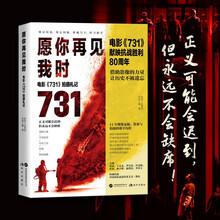下午1时20分破西又响,牯脏旗插在月场正巾,只见乌虐村寨老姚老酸挥舞扯开喉咙,吆喝着:“各村各寨来领簸箕饭哕!”直喊得l声音沙哑,脸红筋胀,双囤瞪,口角翻出白沫。人们一拥而上,一只只粗糙的手用力抓饭着糯米饭,团成团;用剪开肉,蘸着上辣子面吃。成百上千的人流同着簸箕饭涌动,犹如涌起的人浪一潮潮。来者有份,敞开肚皮,吃得心花怒放,吃得汗水泪水往下淌……人们说着笑着,相恭贺着……那份来自内心的喜悦挂在每个人的脸上。<br> 在苗族生活中,簸箕饭不是轻易可见到,也不是轻易肯抬出来宴请外村寨人的。当一个氏族在有了实力、有了骨气、有了竞争能力和底气充足的情况下才可见到如此犬模的簸箕饭阵容。可以这样说,簸箕饭是苗族村寨一个氏族强大的标志。如此以来,饭无形中有了超常的凝聚力。当乌虐村的牯脏户们抬上这宝贝走向寨外时,那写在脸自豪和兴奋,还有不可蔑视的态度显而易见。簸箕饭扫荡了他们以前贫穷的耻辱,他回了自信和做人的尊严,这对苗族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br> 刚来时,就听说今天是个非同寻常的日子,于是,在心里数着日子,期盼着这天的到来。老粮说“营拟”(苗语:“牛旋堂”,就是将牛披红挂彩,人们挑肉送米,穿着新衣去牛堂转==圈,表示炫耀)就在今天午后。在此之前的一个月,每一头牯脏牛都在主人的陪伴下去牛堂角斗。角斗是鼓社祭的序曲,之后牯脏牛便养精蓄锐,关在圈里好吃好喝伺候着,直到今天。这些待宰的牛是在牛堂中英勇搏斗未致伤的牯牛,这样的牛才称得上“斗士”,祖宗们才喜欢。事实上,牛旋堂也是让牯脏牛与它曾奋勇拼杀的牛堂告别,苗人们称这为“追对”。<br> 沐浴着晨曦,在透凉的晨风中,尾随着一大群男人向着寨子后山的一片树林走去。这不是一般意义的砍树,早在鼓社祭之前的一周,各牯脏户便派出娘家屋里的男人上山选树,这种树干呈灰白色,树叶小而圆,苗人们称为“枫树”。按祖规选择双生树,即一个根长出两个主干的枫树,打上印记。就是它了!早上7时30分,老粮带着舅老找到了他们的枫树,由舅舅先用麻绳穿起一条干鱼儿捆在被砍的那棵树干上,意思是年年有余,子子孙孙兴旺。接着在树下,放上三到五碗酒和一碗米。这时舅舅念念有词,又喝一口酒喷向树干,再把剩下的酒倒在树根里,撒上一把米,接着执刀砍下树干。倒地方向一定向东(苗人认为他们祖先由东方而来)。接着将树干锯断成两截,做成两米多长的木桩,一群人抬上,前呼后拥回寨。<br> 上午10时20分,破西响起,各牯脏户开始准备牛旋堂事宜。他们将花被单盖在牛背上,把绸被绒毯搭在竹竿上,抬上“乌儿纱”和“西厚”,还有大米和猪肉。<br> 正午12时,破西再响,芦笙歌起,牯脏头夫妇在那打根哈(苗语:女性护送者)和寨老们的簇一拥下准备出门,神情异常严峻。<br> 可能是由于几天的少吃不睡,也可能是由于场面宏大,过于紧张,老乌已无力独自行走。虽然有老粮和寨老韦老阶架着他移步,他双腿仍然打颤。那些手执古战刀的沟横,瞪着双眼,迈着大侠般的步伐,一路降妖除魔,护送牯脏头,走向牛堂。姚老乌的女人潘老英似乎精神要好些,她盯着地面,在两女人搀扶下一步一步向前;那些身穿黑色布衫的女人们,昂首挺胸在她身后坚实得如一堵墙。紧接着,牯脏牛出圈,鞭炮和土炮响声不绝于耳。每头惊恐万状的牯脏牛几乎都淌着眼泪,喘息着由八人合摁着排成一溜。人们用力地牵引着它们,走在牯脏头夫妇之后。<br> 我夹在人群中,跟着人们奔跑着,想看看牯脏牛泪流的双眼。它们眨巴着红红的大眼,草绳穿过鼻孔,被人们用力揪住,嘴里不时扑出粗气。眼前这些壮实的牯脏牛在告别牛堂之后的黑夜里便要命归黄泉。这是苗人和牛的缘分。它们真的是苗人祭祖最好的道具吗?此刻,我对牛产生了一种痛彻脏腑的怜悯,为牛儿们今夜悲壮的献身暗自神伤。<br> 牛旋堂的过程令见者热血沸腾。牛堂被里三层外三层的人们包围着,当手执牯脏杆的寨老冲开一道口子时,后面庞大的牯脏队如汹涌的江水一下子冲开更大的人墙,直奔牛堂而去。人们拥着牯牛沿逆时针方向开始旋堂。与此同时,牯脏杆再一次插在月场中央,破西、鞭炮声齐鸣,气势磅礴的牯脏队伍在老乌的带领下缓缓旋转二=圈。牯脏牛们拼命地挣扎,人们又拼命地摁住,并依依呀呀地念叨。意思是,逝去的老人家,这些东西还满意吧?现在有米有肉,我们有本事举办鼓社祭,你们脸上有光彩了吧?<br> 中午12时30分,当第一批牛旋堂完毕之后,我见老乌走出牛堂那疲惫的模样,气血耗尽像是抽掉了筋骨的布人,如吐尽了丝的蚕。我现在彻底懂了他的“苦笑”。<br> 下午4时40分,32头牯脏牛分别旋堂完毕,又回到各自的圈中,待时辰一到,杀它祭祖。之后,寨老侯老高站在牛堂中央,挥舞着双手,歇斯底力地喊:“下次——哪个寨子——努牛(吃牯脏)?”于是,距此十几公里的摆底寨的代表大胆而底气十足地回答:“啊哕哟——,我们摆底哟——三年之后,到摆底寨——吃簸箕饭哟呵——”<br> 至此,乌虐村的牛旋堂仪式圆满结束,同时,封芦笙,一封三年不得吹奏。<br> 下午5时,牯脏户开始在沟横的指导下架设“柢”。首先由牯脏头老乌用两根竹棍在老沟横的指点下,于地上定点,即杀牛的位置。接着其他牯脏户相继定点,然后各户在点上挖地洞,约半米深,将两根香枫木桩栽下,交叉捆绑,形成“X”形,继而在交叉点上横着固定一根三米多长的圆木,用以挤压牛头。在这个被苗语称为“柢”的刑架旁,还放有竹圈。老粮说:“这当作银饰要套在牛角上,我们苗人历来喜欢银饰。”他们要让牛儿们死也美丽!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