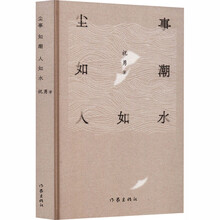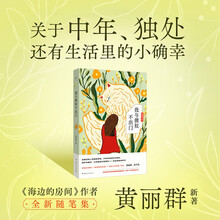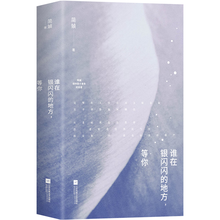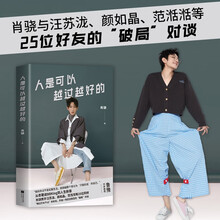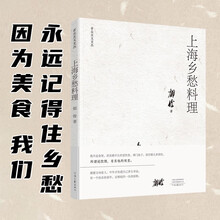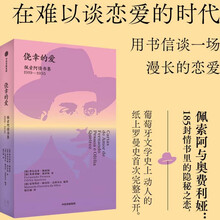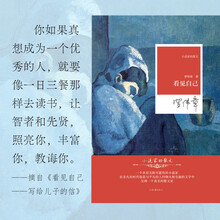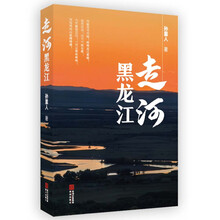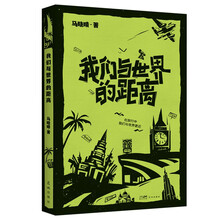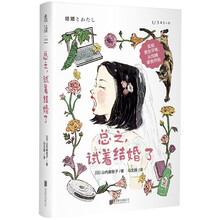一个永不消逝的精灵<br> “杨小凯”这个名字不仅对许多学经济的入耳熟能详,就是对懂政治和关心政治的人也并不陌生,甚至对热心文学作品,喜欢励志故事、“心灵鸡汤”的读者,他也是个很好的“样板”。试想,“高干子弟,造反派,政治犯,阶下囚,自学成才,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大学教授,诺贝尔奖两次获提名者,”皈依基督教,英年早逝“,一个人如果具有这些元素中的任何两三个,皆可构为传奇,堪称人生不凡,而杨小凯却是包含了全部。他的一生充满与众不同的”奇迹“和”矛盾“,他的人生之路充满”非理性“的选择,而他其实是个思想深邃,作风审慎,具有科学和理性思考的人。<br> 杨小凯在事业上的成就如果用诺贝尔奖来衡量的话,他是”华人中距离诺贝尔经济学奖最近的人“,他被赞誉为”世界上最有洞察力和最严谨的经济理论家之一,也是经济学家中最富创造力的思索者之一“。”他的洞察力和批判力同样表现在对社会制度,对人性,对人类普世价值的思考。他说“经济学家要有良心”,“知识分子一定要保持独立的声音”。终其毕生,他拒绝向阻力最小的路上“滑”,守住自己,守住良心,总是逆势而行,向自己心目中的目标挺进。在他五十五岁那年带着令人惊叹,令人痛惜,令人敬佩,令人怀念的不尽情感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br> 从《资本论》开始<br> 我第一次见到小凯是去澳大利亚Monash大学读博士时。那天我找到他的办公室,当时他已经很有名,刚从香港大学访问归来.因为我读过十多年前他写给我父亲的信,此刻满脑子都是好奇和钦佩,还有禁不住的激动和紧张。<br> 我知道他是湖南人,“文革”初期是个高一学生,那年因为一篇大字报,不仅本人遭受牢狱之灾,全家也为此受尽磨难,母亲甚至自杀身亡。他因触犯了“政治”被关押在狱中十年,万幸没有被政治“消灭”,而是刻苦自学了数学、英语和经济学。出狱后,四处求师、求学,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知道了“杨小凯”这个名字。我曾遗憾我父亲不是计量经济学的专家,不能接受这个学生;我曾担心在当时老大学生开始考研究生、研究员,老三届开始考大学,一批批被压抑的人才破土而出的大环境下,这个“自学成才的年轻人”不会被人忽略吧?我关心他能否找到合适的导师,在教授们收到的众多“求学来信”中,他的信该不会石沉大海吧?同时,我也非常好奇,他为什么会选择学经济?如果立志从事政治或做一个政治学研究者不是更“顺理成章”吗?我曾是那么希望能够见到这个“年轻人”,希望他能来到北京,更希望他能如愿以偿重获读书的机会。令人欣慰和鼓舞的是,虽然他在求学和找王作的那段日子里,还是遭遇不少挫折和打击,但是最终没有被忽略,没有被埋没,在往后的岁月里,他的声音在经济学界越来越大,越来越有份量。<br>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