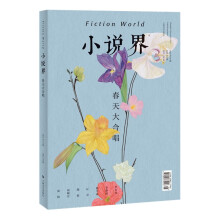这时有一个女青年替我问了,居委会很小心地给秋打电话,说有人来访,那女青年笑说她老人家会见我的,我们约好的,可是我把笔记本丢了,地址也丢了。她满不在乎,当然因为她年轻,她可以找。我跟着她,走过一幢幢有绿地间隔的楼房,来到秋家。那女青年很小心地在门外擦脚垫上擦过了脚,这些麻烦事我是用不着了。
秋的房间很整洁,四壁图书,各种文稿一点不乱,我很佩服,她的风帆还没有收起,那架斯坦利钢琴靠在墙边,它仍然在,还是那么光亮。我想弹起来一定还是那么好听。她坐着,向来客微笑,示意那女孩坐下。那女孩恭敬地鞠躬,呈上一封信,我猜是介绍信,果然是地方上一位教授推荐这女孩来考秋的博士生。女孩说她醉心比较文学研究,如果能投在秋的门下,就此生别无他望了。秋很温和,说她还没有决定今后还招不招博士生,因为还有别的事情要做。如果她招的话,会有招生简章的。她安慰女孩说:“我已经对你有了印象。”女孩又谈了一些对文学的看法,说是要研究对鬼魂的描述,比如说哈姆雷特的鬼魂和聊斋的鬼魂。我听了不觉浑身一颤。
秋专心地听着,后来微叹道:写鬼其实是一种向往,因为人总是要老的要死的。死意味着结束,可是很少人甘心结束,便有了鬼魂。那是很美丽的想像。不同民族对鬼魂的想像是不同的。西方男鬼多,中国女鬼多,你有没有注意?女孩用心听着,不时抬起眼睛看秋,不知为什么忽然满眼含泪,她站起身鞠躬告辞,泪水滴在地板上,连忙用纸去擦。秋温和地说不必了,又亲切地问有什么为难的事吗?女孩默默地从包里取出一份杂志,翻到一页,正是秋的照片,那大概是她五十岁左右的照片,盛需丰容,很有神采。那时她开始成名。秋立刻明白了,轻叹道:“现在是老而丑了,是吗?”女孩点点头,我想她可能想到自己也会变老变丑,这种为难是无人能解决的。她们两人对看了一会,女孩再鞠躬,告辞走了。
秋站起身送她到房门口,又转身走到阳台上坐下,看着窗外。窗外有两棵白杨树,叶子在雨中很绿,很光滑。我发现她走路的姿势很特别,却想不出问题在哪里。阳台上很亮,她的脸上东一块西一块的老年斑好像放大了,还有几处莫名其妙的红色,显然也是病或老所致。我不由得又心头一颤,怪不得那女孩要哭。我的审视一点没有打搅她,她安详地看着白杨树。我不再看她,而去端详墙壁,墙上挂着辛校长夫妇的照片,辛校长在“文革”中猝死,夫人也一恸而绝,当时大家都很震动,现在照片中人还没有老。钢琴上摆着她和丈夫阿潘的照片,照片上俩人都还年轻,靠着一段栏杆,秋的一只脚稍稍抬起,登在栏杆上,很调皮的样子。他们离婚以后,阿潘调到我所在的小城,后来也没有复婚,秋倒还摆着两人的合照。阿潘是十多年前患病去世的,能够自然死亡,算是善终。旁边摆着的照片中是一位时髦女性,眉眼略有些像秋,当然是她的女儿蔚来了。我想她幸亏有女儿,不然这房间里除了她就是鬼魂了。一个中年妇女拿着电话走过来,看上去像是陪伴一类。一手掩住话筒一端问:“先生,接电话吗?”秋接过话筒,显然是工作上有来往的似熟而又不熟的那一类,邀她参加一个聚会。秋辞谢了。她交回话筒,想要站起身,可是右半身似乎动作困难,那陪伴忙放下话筒到右边搀扶她。可是秋用左手拉住陪伴的手,很费力地站起来,说:“好了。”我想她大概曾经中风,或是别的病痛,右侧神经有问题,走路的样子有些特别,也是因上肢引起。
一只喜鹊在树上跳。“嘿,小心滑倒。”原来她在对鸟儿说话。她在窗前站了一会,仍走到书桌前,对陪伴说:“今天上午不接电话了。”她打开电脑,一行字很清楚地显现出来。我很快明白了,这是她的回忆录。现在盛行回忆录,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生活很有价值,不应泯灭,要记下来。这也许是多多益善,怕的是不真实的编造,煞费苦心的涂抹。不知底细的人往往要上当受骗,历史也更难弄清。真的,不要说回忆录,连正式的历史著作也是错误百出。现在所谓的著作太多了,胡编乱造说梦话也算历史著作,还有所谓的“纪实”应该改为“记梦”。想像力倒是挺丰富的,可苦了后人,怎么分辨呢?秋亲历了一些历史事件,应该记下来,她是一个诚实的学者,会记下真相。我怀着极大的兴趣盯着荧屏,谢天谢地,这文字在电脑上慢慢流动,不需要翻阅。
真奇怪,荧屏上显出一个卡通娃娃,围着红肚兜,脚下踩着两个轮子。我略一思忖,悟出那是哪吒,他踩的是风火二轮。只见两轮飞速转动,长长的火焰像一面面旗帜在飘扬。秋聚精会神地看着荧屏,我想不出她和哪吒有什么关系。
哪吒在奔跑,我转过脸去看钢琴上的照片。照片上的阿潘眼睛似乎动了动,他看见我了。这时秋忽然大声说:“你要看吗?你看得懂吗?你先不用看,这是个草稿。”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