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矢眨了眨眼。她已等了许久。透过步枪的瞄准镜,她可以看见三名士兵,就站在萨拉热窝一座山丘上的矮墙边。其中一个正凝望着城市,一副若有所思的模样;一个手上拿着打火机,帮另一个点燃手中的烟。看来,他们压根儿不知道自己已经在若矢的视线里。也许吧!若矢想着,士兵们也许以为自己距离火线很远。那他们就错了。也许,他们以为没有人会有那样的功夫,有办法让子弹射穿横隔在自己与若矢之间的层层楼房。那他们就错了。若矢可以取下他们中任何一个人的性命,说不定两个,这要看她如何做出决定。很快地,她就会做出选择。
被若矢盯上的士兵有充足的理由相信他是安全的。若换成是别人想取他们的性命,他们还是会平安无事的。若矢距离士兵将近一公里,而她的步枪和所有防卫军使用的一样,有效射程范围是八百公尺,一旦超过这个距离,命中目标的机会便微乎其微。对若矢而言,这倒不成问题。她就是有本事,让手上的子弹做别人做不到的事。
对多数人来说,远程射击是一道必须正确结合观察与计算的难题,牵涉到对风向、风速,以及目标距离的判断。除了要计算出与目标之间的距离,还要考虑子弹的速度、下降时间,还有瞄准镜的放大倍率,再运用公式进行计算。这其实就和抛出一个球是同样的道理,不是对准目标投球,而是在经过计算后,沿着与目标物相交错的一道弧线抛出去。若矢不会去计算这些数据。她从不理会什么方程式之类的事,只是把子弹送往子弹该去的地方,如此而已。她不明白为何其他的狙击手竟然做不到。
此刻她正藏身在一栋遭战火焚毁的办公大楼的废墟中。她躲在一扇窗户后方数公尺处,从这扇窗户可以看见城市南方的山峦。不管找谁来看,都不会完全看不见,但很难辨认清楚,在那样的地方竟有个黑发及肩的清瘦年轻女子隐身在烟火不断的日常风景当中。她趴在地板上,腿的一部分盖着旧报纸。那双明亮的蓝色大眼,是唯一的生命迹象。
若矢相信,自己与山丘上的那些狙击手大不相同。她针对的目标向来只有士兵,那些士兵却是谁也不放过,不管你是手无寸铁的男人、女人还是小孩。当他们杀害某个人时,他们所想要得到的,不单单是抹杀一条人命。他们要的是毁掉这座城市。在萨拉热窝消逝的每一条生命——就像迫击炮重创楼房一样——一点一点地削去若矢的年轻岁月。幸存下来的人,失去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同胞,也失去了关于原先生活的记忆。人们不再记得穿越街头时,不会有人从山丘上对着你开枪的那段日子。
十年前,她十八岁的时候,或者说,在她还没被叫做若矢之前,她向父亲借了车到乡间拜访朋友。那是个晴朗、清澈的日子。当时她感觉到那部车好像拥有生命,也好似她与那部车之间的连动是一种命运,而一切正在朝向事情应有的方向前进。她开车转过弯道时,电台播放起她最爱的歌曲,阳光像穿过蕾丝窗帘一样,透过层层的树梢间泄下来,这一切让她想起她的祖母,接着她的眼泪便开始顺着脸颊滑落。她的眼泪并非为了祖母而流。祖母还健在。若矢流泪,是因为她感受到那种受到上天眷顾的生命喜悦,正因为这美好的一切终将有结束的一天,才让这样的喜悦更加强烈。这感受撼动着她,让她得把车停到路旁。过了一会儿,她却感觉自己有点儿傻,所以她从未跟人提起过这件事。
然而现在她一点也不觉得自己傻。她很清楚,自己曾经毫无预兆地闯进生命的神秘核心。能够了解生命的美好与有限,乃是一件来自上天的难得礼物。
因此,若矢扣下扳机,结束视线里那名士兵的生命时,她的理由不单只是要让他死而已。她当然不能否认这个意图,但更重要的是,这些士兵夺走了原先属于这城市里所有人的这份礼物。生命必然有终结这件事,变得不言自明,失去了一切意义。然而对若矢来说,更糟的是,她所理解的一切,与她所相信的一切,两者之间的距离就这样被破坏了。因为就算她知道自己那天的眼泪,绝不是什么青春期女孩荒唐滥情的演出,她也不是真的相信自己领悟到的事。
此刻若矢的目标,在格拉巴察占领区附近的弗拉查。敌人正是以此地一处制高点要塞为据点,在确保完全不会受到反击的情况下,对这座城市进行轰炸。在二次大战期间,弗拉查曾是纳粹监禁、杀害反对者的地方。那些死者的名字就刻在阶梯之上。当时没有几个战士会以自己的真实姓名上战场。他们都为自己取了新的名字。相较于他们酒过三巡后,在酒吧里吹嘘的丰功伟业,这些名字其实诉说着更多他们的故事。然而这些曾经反抗政府的名字,还有他们曾经的事迹,在日后,却被所反抗的政府扭曲成政治宣传的工具。人家说这些人改名换姓,是为了不让自己家人陷入危险,这样一来他们才能在两个身份之间变换自如。但若矢不这样想,她认为这些人改名换姓,是因为唯有如此,才能将个人从自己不得不去做的事情当中抽离。只有这样,那个曾经战斗过、杀戮过的人,未来才有被遗忘的一天。开始是因为别人恨她,她才反过来恨别人,接着因为他人加诸在她身上的种种作为,她恨起了这些人。在这样的反复过程之间,牵引出了她那种抽离自我的欲望。她要将那个会反击别人的自己,从身上抽离。从那个起初从不回击的女孩身上分离出来的自我,将要去享受反击的乐趣。若是她也用了真实的姓名,那么她跟那些丧命在自己手下,有名有姓的人还有什么不同?这样取走的性命,将会重于自己的死亡。
自从第一次拾起步枪杀人,她就开始叫自己若矢。就算有人依旧叫着她的本名,她也充耳不闻。这些人若继续这么喊,她就会告诉他们,她现在的名字是若矢。不会有谁对这件事多说什么,也不会有人去质问她为何这样做。在这里,每个人的作为,都不过是为了求得生存。若还有人继续逼问原因,她会说:“我恨他们,所以我叫自己若矢。而你们以前认识的那个女人,她谁也不恨。”
若矢之所以选上今日的目标,是为了让这些身在弗拉查的人感受到威胁。为此,她不得不进行这难度颇高的攻击行动。虽然藏身这栋残破大楼的九楼,但对方的要塞在山丘上,她必须让子弹穿过她与猎物之间的整排楼房,目标里的士兵必须停留在三公尺见方的空间内。同时,尚在燃烧当中的楼房里冒出的阵阵烟雾,也不时遮蔽着她的视线。一旦她开了火,南方山丘上的所有狙击手都会立刻搜寻她的身影。很快地,他们就会找出她的所在。接着他们会开始炮轰这栋大楼,如有必要会将大楼夷为平地。正因为这是一栋容易出手的攻击目标,大楼才会遭到破坏。一旦行动之后,她逃生的机会可说是微乎其微。不过,这一回对她而言,还不算是多么特别的挑战,过去她也曾在更艰巨的情况下扣下扳机,也面临过对手更快速度的回击。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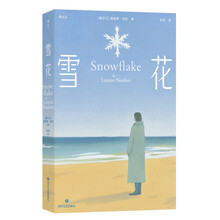
——卡勒德·胡赛尼 《追风筝的人》作者
斯蒂文·高勒威笔下的三人组角色,其形式之精准近平狄更斯式风格:一个代表萨拉热窝的过去。一个代表萨拉热窝的未来,还有一人代表萨拉热窝当下的恐怖与希望。但这本精雕细琢、充满野心的小说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在于它以一种绝妙的力量揭露了生活在围城当时的情感面现实。
——加拿大《环球邮报》
在这本哀伤的小说中,高勒威探究了战争的残暴与音乐的救赎力量。《萨拉热窝的火挝琴手》以让人无法忘却的意象、令人心碎的简洁雕琢而成,强而有力地传达了人类精神即使面对无止尽的绝望仍终将战胜一切。
——《华盛顿邮报》
高勒威以有力的笔风带领读者进入书中的每个角色。他详述他们的每一个思绪、每一个感受,其生动的文笔超越了悲情。《萨拉热窝的大提琴手》的唯一缺点就是它只有两百多页,就如同一场让观众意犹未尽的精彩演出。
——《伦敦自由通讯》
这本深深撼动人心的小说,诉说了萨拉热窝这个残败城市中的居民所承受之惊人磨难与其勇气,以及其不愿向仇恨屈服的善良之心。最强力推荐!
——澳洲《好读》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