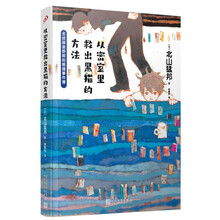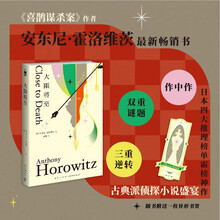一天深夜……
“我经常想,”米克?巴卢说,“如果当时选择了另外一条路,会有什么不一样。”
说这话时我们俩正在地狱厨房①的开放屋酒吧。葛洛根经营这家酒吧已经很多年了。尽管酒吧从里到外的风格都没怎么变,但还是能感觉到旧城改造对这个地区的影响。以前那些难缠的酒客不是死了就是搬走了,眼下的客人要优雅、绅士得多。吧台上供应散装的健力士②,也摆了不少单一纯麦苏格兰威士忌和其他上好的威士忌。但吸引酒客的仍然是这酒吧彪悍的名声。大家指着墙上的弹痕,拿店主臭名昭著的往事下酒。有些故事还真的发生过。
①地狱厨房(Hell’s Kitchen),纽约曼哈顿的一个社区,包括第三十四和第五十七大街之间的地区,大致从第八大街到哈德逊河。
②健力士(Guinness),一种啤酒,产于爱尔兰,是世界著名的黑啤酒。
这会儿酒客们都走了。酒保打了烊,所有的椅子都倒扣到桌面上,省得早晨杂役来打扫拖地的时候碍事。门上了锁,灯都关了,只有我们俩的桌子上方还亮着一盏灯。米克的酒杯里装着威士忌,我的杯子里是苏打水。
这几年,我和他在酒吧夜谈的频率越来越低了。年纪大了,我们都不想搬到佛罗里达去,每天一大早起床去家门口的馆子吃套餐。同样,我们也不想彻夜长谈,再瞪大了眼睛迎接黎明。我们都过了做这种事的年纪了。
他现在喝得比以前少。一年多以前他结了婚,那女人比他小很多,名叫克里斯廷?霍兰德。这桩婚事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只有我太太伊莱恩没觉得意外,她发誓早就看出来了——他也确实因此有些改变,不说别的,至少结婚以后每天晚上都回家了,有个牵挂。他仍然喝十二年陈詹姆森,而且不加冰不加苏打水,但喝得没有以前那么多,有些日子干脆滴酒不沾。“我仍然馋酒,”他说,“但多年以来我一直觉得很渴,现在这种渴离我远去了。我也不知道它去哪儿了。”
早些年,我们倒是经常在酒吧熬通宵,边喝边谈,眼看着天就亮了。偶尔也会沉默不语,各自闷头喝酒。黎明时分,他会系上父亲传下来的血迹斑斑的围裙,去肉类加工区的圣伯纳德教堂望屠夫弥撒。有时我会陪他一起去。
时过境迁。肉类加工区如今是雅皮聚居的潮流之地。大多数肉类加工厂也停业了,原来的厂房变成了饭店和公寓。圣伯纳原本是爱尔兰教区,现在也成了瓜达卢佩圣母的领地。
我不记得上次看见米克系那条围裙是什么时候了。
今天这种夜谈挺少见的,而且我们都觉得有必要留下来谈谈,不然这会儿早该回家了。米克好像有点儿伤感。
“另外一条路,”我说,“什么意思?”
“有些时候,”他说,“我觉得好像别无选择。我是命中注定要走这条路的。可最近我不这么看了,因为现在我的生意干净得像狗牙似的。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说像狗牙?”
“不知道。”
“我问问克里斯廷,”他说,“她会坐下来摆弄电脑,三十秒钟就能告诉你答案。当然了,前提是我得记得问她。”他不知想起了什么,浅浅地笑着。“可当时我没看清,”他说,“我已经变成了一个职业罪犯。当然了,这方面我可不是什么开路人。我们那儿最主要的职业就是犯罪。周围的街道简直是犯罪职业高中。”
“您可是优秀毕业生。”
“没错。如果小偷和流氓真要开毕业典礼的话,我说不定还能代表全体毕业生发言呢。不过,说实话,我们那儿也不是所有人长大都成了罪犯。我父亲就很体面。他是——呃,算了,看在他已经去世的分上,我就不说他是什么了。不过他的事儿我跟你说过的。”
“确实说过。”
“归根到底,我父亲是个体面人。每天早起去工作。我几个兄弟走的路也比我光彩。一个当了牧师——当然,也没当多长时间,他后来不信上帝了。约翰是很成功的商人,社区的支柱。还有丹尼斯,可怜的孩子,死在越南了。我跟你说过吧,我还特意去了一趟华盛顿,就为了在纪念碑上找他的名字。”
“说过。”
“我真的不适合当牧师。我甚至连骚扰那些祭童的兴趣都没有。我也无法想象自己像约翰那样拍完马屁接着数钱。你猜我想干什么?我有时候想,其实当初应该走你这条路。”
“当警察?”
“这想法很奇怪吗?”
“不奇怪。”
“我小时候,”他说,“觉得当警察才是男人该干的正事儿。穿着帅气的制服,站在大街上指挥交通,引导孩子们安全过马路。保卫良民,惩治恶棍。”他咧嘴一笑。“还恶棍呢,真没想到。不过我们那儿还真有男生穿上了蓝制服。其中有一个叫蒂莫西?伦尼的小子,跟我们这些人也没什么区别啊。要是听说他去抢了银行,或是帮放高利贷的人收账,我一点儿都不意外。”
我们又聊了一会儿。聊当初的选择,以及一个人到底能有多少选择。后一个问题需要时间思考,于是我们都沉默不语。然后他说:“你呢?”
“我?”
“你不是从小就立志当警察吧?”
“的确不是。这事儿我从来没计划过。那年头警校的入学考试特别简单,只要去考都能考过。我就这么上了警校。然后就当上警察了。”
“你会不会走相反的那条路呢?”
“你是指走上犯罪道路?”我想了想,“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因为我也没有天性纯良到那种程度,”我说,“不过我得说,我好像还真没有受过那方面的诱惑。”
“真没有。”
“我小时候住布朗克斯,有个跟我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我回忆说,“后来我搬家了,我们就再也没有联系。过了几年,我又遇见过他几次。”
“他走了另外一条路。”
“是的,”我说,“他在那行也不太成功,不过他走上这条路也是很自然的。我透过警局的单面镜见过他一次,然后又失去联系了。后来又过了几年,我和他又联系上了。那会儿咱们还不认识呢。”
“那会儿你还在喝酒吗?”
“不喝了,不过当时刚戒没多久,还不到一年。他的事儿说起来还挺有趣的,真的。”
“说呀,”他说,“别卖关子。”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