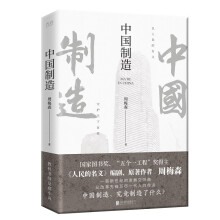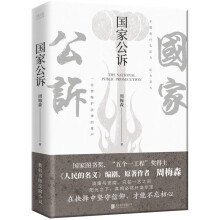越来越多的消息像风吹在水面上似的,一波又一波地灌进宋德顺的耳朵里。他的心里就像平静的湖水投进一块巨石一般,不可能不泛起一圈又一圈的涟漪。他很快就要升任东原市档案局一把手了,尽管这是传言,但他绝对相信社会上业余组织部长的话,因为他们的说法最后往往被无情的事实所证实。
以前,在他身上也曾有过两次由副职变正职的传言,但都水月镜花空喜欢。原因很简单,就像人们说的,生命在于运动,当官在于活动,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他既没跑又没送,自然是原地不动了。
宋德顺在二十几年前的一次招工中甩掉了农民的帽子,由于他的实干精神和业务能力的提升使他很快从乡里调进了档案局,而后又顺风顺水地当上了副局长。他不善交际,业余活动很少,曝管成了业务尖子,可副局长这个位置一坐就是十来年。六年前,不少人纷纷告诉他,市里就要去掉他那个“副”了。他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里却着实高兴了一阵子。没想到走了老局长,来了个并不年轻的新的老局长。
三年前,那位新的老局长退休了,社会上疯传他要接班,最后宣布的结果还不是他,是现在这位又要退休的局长。这次又涌起他扶正的消息,尽管说他不是官迷,也绝不是毫不迷官,但心里自然不会没有些想法。
的确,档案局这么个小单位,无权无势无财力,人们都不看好,也没有谁哭着喊着打破脑袋地往里钻,但它毕竟是…个标准的正处级架子,好歹都是公家的事,但工资增加、职位提高却是自己实打实的利益。
在社会上,尽管他牛不起来,可一进局机关的院子.关起门来照样能吆五喝六。再者说,宁当鸡头不当牛尾,当了一把手绝对不会再看别人的脸子。副职嘛,就不好说了,再好的思路,再好的想法,只要人家正职摆摆手摇摇头,你再高明的东西也全都得放到一边歇着去。
宋德顺倒不一定有这么多花花肠子,要有早提了,可现在讲究按劳取酬,按付出收取回报。他想把事干好,也想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最不济也得付出与回报相等。现状是,老局长凡事一推六二五,不管三七二十一。他任副职,干的却是正职的活儿,除了不能拍板,不能作决定之外,啥事都得他忙乎,心里不窝屈才怪了!
这次是第三次传言了,能否把传言变成现实,能否迈过由副职转为正职的这道坎儿,这次怕就是最后的机会了。别忘了,他已经四十七岁了,七上八下,过了五十就准备奔赴二线的队伍行列之中了,因此,他必须抓住这次机遇。
红日临窗,老宋比往日还早地进了办公室。机关里大部分人还未到,他提着两只暖瓶到锅炉房打开水。回屋铡沏好茶,点起支香烟慢慢品味着。电话响了,老局长请他过去,告诉他下午市委组织部金承金部长要来找他谈话,说白了就是任命前的最后程序,除了思想上做些准备外,晚上还要安排个饭局,好好接待一下。
一整天,宋德顺紧张着、兴奋着,在焦急和烦躁中等待着、切盼着。快要下班了,金部长还没动静,他心里有些着急,都一天了,压根儿没这么浮躁过,尽想着部长那张脸、那张嘴,生怕招待不好,部长耷拉了脸,撅高了嘴。
其实,老宋想多了。老局长可能感到宋德顺这么多年来,不争名利不争权,像头牛似的默默干活儿,任劳任怨地不容易,自个儿临退了,也该帮他…把了,让办公室胡英主任把该安排的都安排妥当了,还格外嘱咐说,金部长歌不爱唱,舞不爱跳,见了麻将走不动道,只要让他玩尽兴了,啥事都好办。怎么尽兴?牌桌上的事还用挑明了说吗?
金部长没有到档案局,一大早就去了省里。省委组织部干部处王处长的一个电话就让他颠儿颠儿地进了城。按理说王处长的职务比他低,但人家萝卜不大长在了辈儿上,管的就是市地县级领导,升迁任降都经他们的手,甭管吃啥面都得过他们这一水。几句好话可能让你高官得坐,几句谗言又会使你丢职罢官。何况除了工作关系之外,他俩又有外人不知的私人交情呢!这急风急火地叫他来肯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而且又必须面谈,不可在电话里大呼小叫地瞎嚷嚷。谁知进了王处长办公室并未见人影,按处里人员告知的地点,又折转到一家星级大酒店。
金部长进了大厅,在服务员的引领下来到了一个豪华套间。王处长正在和几个大腹便便的人打麻将。王处长很热情,为他一一介绍了几位国企老总,说:“甭急,好酒不怕远,好饭不怕晚嘛!”金部长心领神会,笑了笑坐在王处长身后,当起了免费观众。
王处长牌运很好,才抓三轮牌就叫听了。
服务小姐趁倒热水的工夫,余光一瞥说:“您这牌跑不了啦,很可能自摸!”
王处长满脸带笑说:“观棋不语吧!”不过吉利顺耳的话谁不爱听?“谢谢你啦!”说着利索地抓起一张牌,用手指使劲一抠,用力往桌上一摔,“和了!”服务小姐似乎很得意,扭着屁股笑着走了。
四圈牌结束后又重新掷点找庄,再开战局。这轮牌王处长手气并不好,起手牌样样有,风头进出不断,而且像只只养熟的鸟儿跟他投缘似的,放出去又回来,总也打不完。好不容易弄得有点儿眉目了,别人早就守株待兔了,他一出牌立刻就有人和了。他心里有了气,连连骂自个儿手臭,好像从粪堆里拔出来没洗手似的。忽然,他憋了把大牌,叫听后不巧又抓了张五万。常打牌的人都有预感,感觉到了这张牌的危险。这把牌若是和了就可以弥补前边的亏损,可放出去点了炮便是雪上加霜。这张奥五万让他为难了,这是张加倍翻番的牌,留着无用,打出去又太危险,真像个饿汉子抓住个烫山芋,吃不下扔不得。他不能不慎重。金部长说了句:“跳河一闭眼,生死由命呗!”王处长似乎有了信心,啪地扔进了桌中央。“和了!清一色、捉五魁、一条龙!”一个老总眉飞色舞地嚷道。亏他身体健康,若有心脏病,说不定当场就激动地挺了尸。
王处长脸子一下变得阴黑:“好你个金承金,徐庶进曹营你一言不发,放了个屁让我血本无归!”
其实,即便金承金不说,他也得往出打。一则,他自身憋了把好牌,不可能轻而言弃;二则,金承金一句话,不但坚定了他扔五万的决心,而且替自己找了借口,为点炮的责任找了个替罪羊。自己生自己的气没啥道理,若生别人的气,尽管不该也显得硬气。于是,他理直气壮地生气了!
“王处长咋啦?怎么当上了炮兵团长?”一个老总笑了,王处长脸儿拉得更长了,不但阴黑而且有霾。
金承金看着王处长的黑脸儿,盯着牌桌上那张五万,颇多感慨:“五万五万双刃剑,既能为己获利,亦能将别人害惨。就像组织部长的作用一样,既能为别人扬名,也能让别人丢官。金承金呀金承金,你咋就管不住自个儿这张嘴呢?”
金承金愣了一会儿说:“我去趟卫生间。”
王处长连哼都没哼一下。不大工夫金承金又坐在王处长身旁。见他又来了,王处长刚露出阳光的脸又阴云密布。金部长笑了笑依然未动,趁着别人不注意,悄悄把两千元塞进了他的口袋。王处长不动声色,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在偷着乐。过了一会儿,王处长似乎打了兴奋剂,手气也跟着衣兜里的底气一样上升,连续和起牌来,而且越和越大,不但把以前的亏空全部补齐,而且还大面积丰收。他脸上云开雾散,话也多了,说:“咱不是炮兵团长,是税务局长,碰到这么好的纳税人,岂有不收之理?”
牌局一散,屋子里只剩下王处长和金承金。
“老金呀,今几个你这雪中送炭,我这儿就锦上添花了,不然我非一败涂地不可!这钱你拿回去,反正咱也没亏空!”王处长说着点了两千元往桌前一推。
“王处,这算啥呀?我的就是你的,你的还是你的,你这是按劳取酬,劳有所获嘛!”金承金双手把钱又推了回去。
王处长笑了笑没动钱,也没再往外推。
“老金呀,省里有可能提你当市委副书记,在这些日子里,请你务必注意,千万不要让机会从指缝溜走!你知道,这个位置可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盯着,也不是一天两天地盯着,我可是为你尽了心出了力,尽心出力的话我就不说了,咱可是真心地盼你高升呀!”
“王处,咱哥俩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交情啦,今天来得急,没啥准备,改天再登门拜谢吧!”
“这是啥话?太见外了!咱俩谁跟谁呀?这样吧,如果没啥急事,晚上吃完饭再走,有兴趣的话咱们再找几个人来干它一个通宵!”
“不啦!不啦!”金承金突然想起还要去档案局找宋德顺谈话,如不是约好了的,他还真想上桌子过过手瘾呢,尽管他知道这是场不公平的牌局,不用上桌就早已决定胜负,但他还是乐意玩。这是多少人梦想着送都送不出的礼,他不能不送。其实送出的礼是有数的,而收获却是不可预料的。
下班了,档案局的员工往外走,金承金部长却往里走。因为没有接到金部长不来的电话,所以宋局长、胡主任和办公室的人一直都按兵不动。
“进啦!进啦!”办公室的愣头青小张气喘吁吁地跑进办公室。
“你有病啊?什么紧啦紧啦的!把舌头捋直喽再说话好不好?真是的!”胡主任冲着小张直吼。
“金部长进门了。”小张终于说明白了,别人也听清楚了,一窝蜂似的跑到楼口。
宋德顺耐心等待了一天的谈话,仅两支烟的工夫就结束了。金部长起身要走,宋副局长赶忙拦住。
“部长您那么忙,难得到我们小庙来一趟,我已安排了晚饭,饭后他们提议打打小麻将,请部长赏脸就与民同乐吧!”
“好吧!盛情难却嘛!只是我牌技不入流,手又自大一点,那就请你们像日本人一样,多多关照吧!”金承金心里清楚得很,饭局牌局都是关系局,像他这样在此地一跺脚三颤的主儿还能吃了亏?说不定把送给王处长的钱又补了回来。想到这儿便又笑着说:“老宋呀,只听说你是业务尖子,没想到还是麻将高手呀?”
宋德顺也笑了,说:“不瞒您说,我呀是做饭糊,炒菜糊,连熬稀粥都能糊,就是打麻将不和!”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