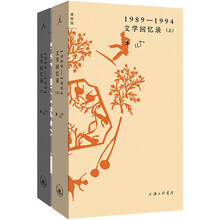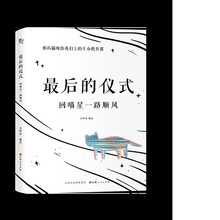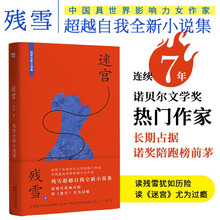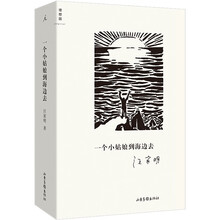这显示了汉奸的花言巧语的作用。
然而,假使出于不得已可以作为辩解的话,那我们要问:当日同样在不得已的情形下,为什么会有许多文人崛起抗清,慷慨就义呢?为什么会有许多文人遁迹山林,终生不出呢?这些人并没有用出于不得已为藉口而投敌附逆。他在诗中用了陆龟蒙的典故,然而隐居甫里的陆龟蒙,不是曾拒绝了高士的征召吗?他在末尾自比于陶弘景,这明明是说:他自己在福王时已辞去官职,已非明之官吏,出仕满清,并非不忠于明室。他本意是叫人“休笑”,不知欲盖弥彰,反而在诗尾露出狐狸尾巴来了。
其实呢,一群汉奸们,大抵都是善于望风转舵,首尾两端。既工于卖国求荣,以享乐于生前;也工于粉饰洗刷,以求谅于后世。吴梅村的《自叹》,目的就在后者。这不仅吴一人为然,就连那明末头等汉奸文人钱谦益,他在南京自动上表,迎降清军,理应是没有什么不得已了,然而他在人清以后,却又常常不忘纂修明史,他希望有人著成一书,来“上答九庙,下诏来兹”,并在所用的印章上,刻着“鸿朗笺龄,白头蒙叟”八字。上句明明表示着大(鸿)明(朗)长寿(笺龄),下旬则又自附于孤臣逸老。这意思很显然,也不外是想用以蒙混世人而已。
这是“二臣”的矛盾,也是“二臣”的悲哀。
但在今日看来,古人还实在未免淳厚一点。为吴梅村计,与其写什么《自叹》、《吊侯朝宗》、《贺新郎》一类的诗词来曲曲折折隐隐约约地表现他的不得已的心迹,倒不如明明白白说自己是“曲线救国”,或干干脆脆自称“地下工作者”,根本否认自己的一切罪过,并没有什么要求谅于人。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