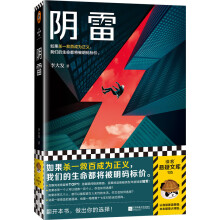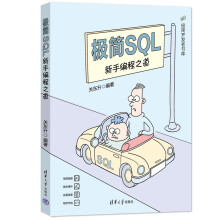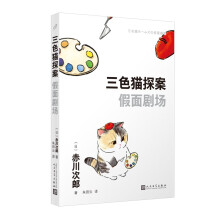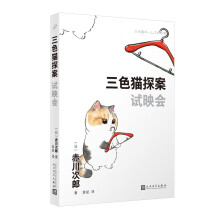刘庆邦说,他喜欢雨天,也喜欢雪天,这个时候他的思绪能飘到很远,有无尽的联想和人生的感触,他将这谓之“走神”,并且说寻求走神成了他的一种自觉。联系到创作,他认为一部作品要做到“抓人”还比较容易,要做到放人(即“走神”)就不那么容易了。在我看来,刘庆邦的一些好作品,其特点就在于能“抓人”,能“放人”。“抓人”,是因为它们大都有个逻辑(合理性)严密的故事圈,一条动人的趣味线;“放人”,则因为它们有个内在的诗化结构,有很强的表意性、抒情性,能与整个人生体验沟通起来。这尤其体现在他的短篇中。若论艺术的纯度和意境的优美,他的短篇高于中篇。真实朴素是他作品的外貌特征,但并非那种直向的朴素,他的朴素带有一定的扩张性。就是说他追求象外之象,味外之味。读《曲胡》《夫妻》《窑哥儿》等篇,常可见到在叙事的空白处,有情绪的游动,联想的触手,把读者带到更开旷的境界。
语言像生活一样,天天在变,倘若墨守某种语言规范、词语规范、句式规范,就很可能使作品蒙上一层尘埃,有文物感。刘庆邦的语言意识敏锐,他能及时捉住生活化的最新语汇,使对话充满俗趣,还能发现一些微妙的语言习惯。例如,冬天的“家属房”有冰溜子,路滑,来人不免跌跤,“他们只小声说了一句我操,就很快地爬起来了”。这种无人称情状,不是我们很熟悉也很滑稽的吗;又如党委书记总爱对人说“找时间好好聊聊”,而这“好好聊聊”又总是引而不发(《胡辣汤》)。这样的例子真是俯拾即是。更强的还是他的叙述,干净、利索、有黏性,善于创造悬念,虽然没有中断、倒错、闪回之类的手法,比较平实,但在叙述的夹缝中常常冒出氛围,带出意蕴。《大平原》中的写麦田和夏夜,《宣传队》一开头写演出结束,就夹上一句:“大团的凉气正从土路两边的麦田里涌出来”,都是例子。刘恒认为他的叙述控制力好,分寸感恰当,如不高贵的好酒,喝起来过瘾,大约不是为了捧场。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