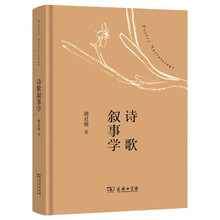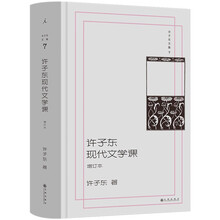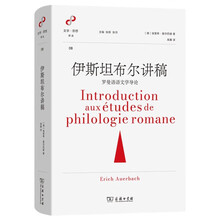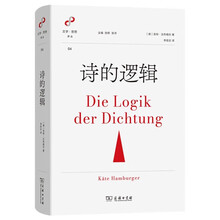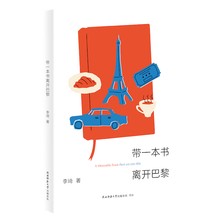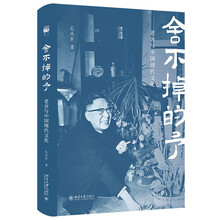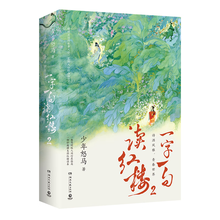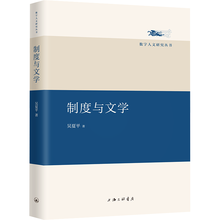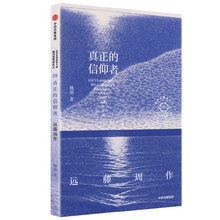需要说明的是,尽管今人沿用《尚书》的既有词语来指称范畴,但在中国古代,它原本是另有称名的,那就是与“实”相对的“名”。先秦时“名实之辨”大兴,儒家重视“必也正名”,墨子针对性地提出“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②其它各家如《庄子·逍遥游》也说“名者,实之宾也”,《公孙龙子·名实论》又说“夫名,实谓也”,大抵都对此两者作了分疏。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后期墨家。墨辩之论“名”、“辞”与“说”,《经说上》说:“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名实耦,合也”。《经上》并有“名,达、类、私”的讨论,其中“达名”作为“有实必待之名”,具有普遍性,就意同今天讲的范畴。荀子说:“名也者,所以期累实也;辞也者,兼异实之名以论一意也;辩说也者,不异实名以喻动静之道也”,又说:“故万物虽众,有时而欲徧举之,故谓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有时而欲徧举之,故谓之鸟兽。鸟兽也者,大别名也”,③这里的“大共名”,同“达名”,在突出范畴须“制名以指实”的同时,更对“名”的类别以及如何达成“名”与“实”的统一作了探索。所以,自本讲开始,我们经常会用“名言”这个词来指代范畴。当然,在用这个词时,更多是从范畴的表达形式着眼的。④
展开